鏡像里的烏托邦:豐塔納與皮斯特萊托穿越時空的“實驗劇場”
日期:2025-03-24 10:21:18 來源:net資訊
訪談
>鏡像里的烏托邦:豐塔納與皮斯特萊托穿越時空的“實驗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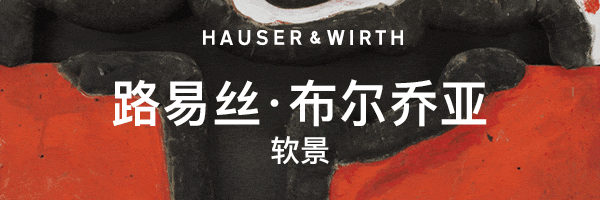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前景中:Lucio Fontana,《空間環境》和《空間概念》系列,1950年,米蘭盧齊歐·封塔納基金會;背景中:Michelangelo Pistoletto,《地球儀》(《減少的物品》1965-1966年), 1966-1968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
“?人類發展出了新的意識,它使得我們不再需要對一個人、一座房子或者是自然界的東西進行描繪,相反它允許人們通過想象來產生空間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盧奇歐·豐塔納(Lucio Fontana)和其他的藝術家一起寫下了這段話。作為當時歐洲最為先鋒的藝術家代表,他們在尋找一個新的開始,一種可以運用與激發想象和潛意識的藝術語言。這一時期,豐塔納開始創作《空間概念》(Concetto Spaziale)系列作品,其中便包括第一批穿孔畫(Buchi)作品——用一把打孔器,在數百年來未被侵犯的畫布上,穿刺出星星點點“丑陋而扭曲”的孔洞。作品脫離了平坦畫布的表面,通過直接利用物理屬性及其周圍的空間來創建圖像。透穿的孔洞暴露出未曾示人的背后空間,而它們本身便是“虛空的第一維度——藝術家和人民的自由,以任何方式創造藝術。”(Lucio Fontana, 1966)豐塔納希望,面對他的作品,觀看者能夠無拘束地追隨自己的想象,不受限于具體形態。“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從左至右:Michelangelo Pistoletto,《地球儀》(《減少的物品》1965-1966年), 1966-1968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1961年,米蘭盧齊歐·封塔納基金會;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黎明時分,威尼斯一片銀色》,1961年,私人收藏;Michelangelo Pistoletto,《人像》,1962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這一系列穿孔畫正是米開朗基羅·皮斯特萊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最初親眼所見到的來自豐塔納的作品。彼時,作為一名就讀于阿曼多·泰斯塔(Armando Testa)廣告設計學校的學生,皮斯特萊托敏銳地意識到豐塔納的創作正在進入繪畫的另一個層次,他開始向往一種自由,就是將藝術用任何一種材料,用自己想用的形式來進行表達。1955年之后,皮斯特萊托以《自畫像》(Autoritratti)系列與《鏡畫》(Quadri specchi-anti)系列逐步確認了他早期的藝術語言,對于藝術家來說,“真正的核心是觀眾、其鏡像與畫中人物之間瞬間建立的關系。” 他用透明顏料營造出獨特的反光效果,又用拋光不銹鋼等自然材料取代了顏料,借助鏡子反光的物質屬性,突破畫布的平面維度。在解釋自己是如何通過鏡面材料去消解藝術與現實之間的界限時,皮斯特萊托明確提到了豐塔納揭示畫布背后世界的理念和方法,正如他所回憶的:“與豐塔納相識后,我開始尋求自己的身份認同。我在鏡子里進行這項探索,通過自畫像來實現。但如果沒有鏡子,就無法存在自畫像,因此,鏡子很快便成為了我個人獨特新視角的主角。”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人像》,1962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盡管豐塔納對于皮斯特萊托的影響顯而已知,兩位意大利藝術家(豐塔納為阿根廷裔)彼此相識,曾就彼此的創作及其與藝術史的關系進行過交流,而作為觀者的我們也能夠以個人視角在他們的作品中覓得一些相互貫連的思想,他們的藝術實踐卻很少被聯系在一起進行探討。事實上,此次于3月20日上海Prada榮宅開幕的新展正是這兩位先鋒藝術關鍵人物的首次雙人展。“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Mirroring: Lucio Fontana and Michelangelo Pistoletto)匯集了兩位藝術家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26件作品——隸屬于彼此迥異的作品系列,強調他們對新表現形式的追求,以及對傳統材料、方法和主題的反叛,以突破個人藝術風格統一性的教條與既定的藝術范式。他們對物質性與藝術的概念維度、表演性空間的探索,以及作品中超現實性的體現,皆在展覽中有所呈現。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人像》,1962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盡管豐塔納對于皮斯特萊托的影響顯而已知,兩位意大利藝術家(豐塔納為阿根廷裔)彼此相識,曾就彼此的創作及其與藝術史的關系進行過交流,而作為觀者的我們也能夠以個人視角在他們的作品中覓得一些相互貫連的思想,他們的藝術實踐卻很少被聯系在一起進行探討。事實上,此次于3月20日上海Prada榮宅開幕的新展正是這兩位先鋒藝術關鍵人物的首次雙人展。“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Mirroring: Lucio Fontana and Michelangelo Pistoletto)匯集了兩位藝術家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26件作品——隸屬于彼此迥異的作品系列,強調他們對新表現形式的追求,以及對傳統材料、方法和主題的反叛,以突破個人藝術風格統一性的教條與既定的藝術范式。他們對物質性與藝術的概念維度、表演性空間的探索,以及作品中超現實性的體現,皆在展覽中有所呈現。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碎布墻》,1968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碎布墻》,1968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
繼展覽首個空間中所呈現的紙本和布面作品《空間環境》與《空間概念》之后,上文所述的創作追求在豐塔納以青銅所鑄的《空間概念:自然》(Concetto Spaziale, Natura)系列和畫布與漆木構成的《小劇場》(Teatrini)中形容盡致。時光倒轉回1920年代,豐塔納的藝術生涯開始于雕塑領域,與其所接受的雕塑與雕刻技術的專業訓練一同行進的,是他對宇宙、空間與未來滿懷熱情的思考。“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前景中: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小劇場》,1965年,私人收藏;背景中: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小劇場》,1965年,米蘭盧齊歐·封塔納基金會;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自然》1959-1960年,私人收藏《空間概念:自然》誕生在一個以征服宇宙為目的,信仰人類無限智慧的時代,藝術家以一種近乎原始的手法,在表面粗糲的球體的頂部與正中施以“割裂”,使其既像是一種異域植物的種子,又似某種外星生命體,裂開一張從空間的深處凝望著我們的臉。他不執著于“美”,也似乎并不想談論“藝術”,而是專注于形式和宇宙中物質的具體化與空間概念的表達。在生前最后一次的訪談中,豐塔納說道:“五百年后,藝術將變成某種好奇心的產物,就像史前人類將兩塊石頭擺放在一起…… 當人類踏上宇宙之旅,他們只會專注于探索空間,發現那些令人驚嘆的奇跡——以至于我們今日所珍視的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空間概念”,這是豐塔納通往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的道路,它比可想的創造更為宏大,比眼前所能看到的更沒有盡頭。雖然這個擺脫“藝術”、地球,乃至所有束縛的世界尚未到來,但這種對烏托邦境界無窮盡的期待仍在皮斯特萊托的創作和社會活動中不斷地被塑形成更為實在的模樣。手繪于鏡面上的《我-你-我們》(Io, Tu, Noi)與《第三天堂》(Terzo Paradiso)以三環無窮符號為標志,象征著在平衡中實現的“人類的第三階段”——自然、人類與科技之間達成和平的新時代,一切對立皆可轉化為統一。“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第三天堂的符號》,2003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Michelangelo Pistoletto,《我——你——我們》,2003-2023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第三天堂”不僅反復出現在他的作品中,也是皮斯特萊特自1996年于家鄉創立的藝術城市-皮斯特萊托基金(Cittadellarte Fondazione Pistoletto)幾十年來持續活動的核心愿景。就在不久前的2月21日,現年92歲的皮斯特萊托正式獲得今屆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縱覽此次展覽所捕捉到的皮斯特萊托70余年創作生涯中的幾個階段,無論是早期的《鏡畫》系列,反法西斯商業主義的“貧窮藝術”(Arte Povera)的代表作《減少的物品》(Oggetti in meno)系列,還是《第三天堂》,我們或許便能具象化地感知藝術家一貫所秉持的“藝術必須推動根本性變革”的理念,以及他為此所做的努力。“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無限立方體》(《減少的物品》1965-1966年), 1966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鏡像”開幕之際,在與現任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惠特沃斯美術館(The Whitworth)館長的策展人李淑京(Sook-Kyung Lee)采訪中,我們了解到,先于展覽的籌備前期,普拉達基金會(Fondazione Prada)團隊已經與皮斯特萊托針對這一雙人展的提議進行了多年的探討和研究。在接到策展邀約的時候,李淑京幾乎在第一時間確信,這次的展覽會在既有的世界藝術史脈絡中梳理出全新的敘事;“鏡像”對于她個人而言同樣意義非凡——早在32年前,她就擔綱策劃了皮斯特萊托于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的首次韓國個展,那是她作為職業策展人的一個重要起點。Q:這次展覽所選擇的作品的材料和類型都十分豐富,創作時間跨度也比較大,您是如何平衡作品之間的相似與差異性的?A:我希望強調實驗性在戰后意大利及國際藝術界中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兩位藝術家都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們創作的核心正是對既定的藝術范式的質疑和挑戰,尤其體現在材料和媒介方面的突破。他們之間的代際差距也構成了有意思的對比,從中我們既能感受到一種演變,又能看見一種延續。總而言之,將兩人的作品并置的結果非常有趣而有意義,展覽強調兩人所共通的對于空間環境與和現實世界的關注,同時呈現了他們各自獨特的創作語言和方法。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從左到右:Michelangelo Pistoletto,《墻的另一面》,2024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自然》1959-1960年,私人收藏Q:藝術家皮斯特萊托參與到了展覽的策劃當中嗎?他對于以展覽的形式與豐塔納建立對話有什么個人的看法嗎?A:皮斯特萊托對藝術史有著深厚的理解,他的創作語言是高度概念化的。他時常以批判性的視角討論和書寫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在我看來,他將這場雙人展視作一次在歷史脈絡中表達自己藝術觀念的機會。Q:作為展覽空間,榮宅自身擁有非常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建筑風格。在這次的策展工作中,是不是有許多針對場域特點的考量?可以舉幾個例子嗎?A:榮宅是一座極富魅力的建筑,其鮮明的歷史和設計特點讓人無法忽視。我在深入了解這座宅邸的過程中,意識到展覽應當向其歷史致敬,而非對抗建筑本身。因此,策展充分擁抱了它所有的細節,甚至包括建筑保護所涉及的一些限制。我們與豐塔納基金會(Fondazione Lucio Fontana)及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密切合作,精心挑選了一系列作品,使其既能與榮宅的厚重歷史氣質相符,又能與建筑內部精美的木質細節和裝飾元素相得益彰。“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餐桌畫》(《減少的物品》1965-1966年),1965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Q:請問皮斯特萊托的《人像》(Figura umana, 1962)與《當下——背身人像》(Il Presente - Uomo di schiena, 1961)在展覽中的具體位置?我們想就此探討一下觀眾介入作品的方式。A:這兩件作品被安放在展覽的首個空間——榮宅曾經的宴會廳內,這里有一頂極為壯觀的彩繪玻璃天花板。《人像》和《當下——背身人像》模擬著我們的觀看姿態,仿佛畫中人物也在與我們一起凝視著眼前的空間。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豐塔納1948至1950年間的一系列“空間概念”(Concetto Spaziale)與“空間環境”(Ambiente Spaziale)紙面作品則呈現著他與空間有關的多種探索。這個空間無疑奠定了展覽的主題,即通過兩位藝術家的代表性作品展開對話。“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當下——背身人像》,1961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Q:對于兩位藝術家來說,表演性都是重要的創作理念。這種表演性的概念是否影響了本次展覽的策展方式?A:當然。我不希望以靜滯的狀態呈現他們的作品,而是希望它們能夠成為動態環境中有機的組成部分。比如,皮斯特萊托的鏡子表面消解了藝術本身與周圍空間的邊界,這一特點引導著布展的具體位置和方式。作品也因此形成著一些關鍵節點,同樣也塑造了平行和包圍等多種空間關系。Q:正如您所言,豐塔納試圖超越這堵墻(transcends the wall),皮斯特萊托則拆除了這堵墻(dismantles that wall)。除了寓意藝術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隔閡,這里的“墻”是否可以被理解為某種對社會、政治或文化屏障的隱喻?A:豐塔納曾往返于阿根廷和意大利,在戰亂與政治動蕩中進行創作,而皮斯特萊托也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與經濟變革。雖然兩人都沒有直接涉足政治,但他們的藝術語言卻激進無畏。并非所有的藝術都需要成為隱喻,但藝術的確可以感應和指引時代。“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小劇場》,1965年,米蘭盧齊歐·封塔納基金會Q:豐塔納曾設想“藝術的終結”,皮斯特萊托則以創作期冀人類文明的新階段。在2025年,我們應如何解讀他們各自的理想主義?您是如何理解和想象“烏托邦”一詞的?A:在他們的藝術中,我看到的是對未來可能性的展望,這種展望積極而充滿能量。對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未竟之事的探索,使兩位藝術家的理想主義得以具象化。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不僅是一個基金會,更是一個賦能的平臺,在這里,他與年輕的藝術家和創作者們慷慨地分享自己對于美好世界的愿景。他的信念——藝術的力量——似乎始終居于這一實驗性的共享空間的中心。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從左到右:Michelangelo Pistoletto,《墻的另一面》,2024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自然》1959-1960年,私人收藏Q:藝術家皮斯特萊托參與到了展覽的策劃當中嗎?他對于以展覽的形式與豐塔納建立對話有什么個人的看法嗎?A:皮斯特萊托對藝術史有著深厚的理解,他的創作語言是高度概念化的。他時常以批判性的視角討論和書寫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在我看來,他將這場雙人展視作一次在歷史脈絡中表達自己藝術觀念的機會。Q:作為展覽空間,榮宅自身擁有非常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建筑風格。在這次的策展工作中,是不是有許多針對場域特點的考量?可以舉幾個例子嗎?A:榮宅是一座極富魅力的建筑,其鮮明的歷史和設計特點讓人無法忽視。我在深入了解這座宅邸的過程中,意識到展覽應當向其歷史致敬,而非對抗建筑本身。因此,策展充分擁抱了它所有的細節,甚至包括建筑保護所涉及的一些限制。我們與豐塔納基金會(Fondazione Lucio Fontana)及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密切合作,精心挑選了一系列作品,使其既能與榮宅的厚重歷史氣質相符,又能與建筑內部精美的木質細節和裝飾元素相得益彰。“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餐桌畫》(《減少的物品》1965-1966年),1965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Q:請問皮斯特萊托的《人像》(Figura umana, 1962)與《當下——背身人像》(Il Presente - Uomo di schiena, 1961)在展覽中的具體位置?我們想就此探討一下觀眾介入作品的方式。A:這兩件作品被安放在展覽的首個空間——榮宅曾經的宴會廳內,這里有一頂極為壯觀的彩繪玻璃天花板。《人像》和《當下——背身人像》模擬著我們的觀看姿態,仿佛畫中人物也在與我們一起凝視著眼前的空間。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豐塔納1948至1950年間的一系列“空間概念”(Concetto Spaziale)與“空間環境”(Ambiente Spaziale)紙面作品則呈現著他與空間有關的多種探索。這個空間無疑奠定了展覽的主題,即通過兩位藝術家的代表性作品展開對話。“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當下——背身人像》,1961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Q:對于兩位藝術家來說,表演性都是重要的創作理念。這種表演性的概念是否影響了本次展覽的策展方式?A:當然。我不希望以靜滯的狀態呈現他們的作品,而是希望它們能夠成為動態環境中有機的組成部分。比如,皮斯特萊托的鏡子表面消解了藝術本身與周圍空間的邊界,這一特點引導著布展的具體位置和方式。作品也因此形成著一些關鍵節點,同樣也塑造了平行和包圍等多種空間關系。Q:正如您所言,豐塔納試圖超越這堵墻(transcends the wall),皮斯特萊托則拆除了這堵墻(dismantles that wall)。除了寓意藝術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隔閡,這里的“墻”是否可以被理解為某種對社會、政治或文化屏障的隱喻?A:豐塔納曾往返于阿根廷和意大利,在戰亂與政治動蕩中進行創作,而皮斯特萊托也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與經濟變革。雖然兩人都沒有直接涉足政治,但他們的藝術語言卻激進無畏。并非所有的藝術都需要成為隱喻,但藝術的確可以感應和指引時代。“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小劇場》,1965年,米蘭盧齊歐·封塔納基金會Q:豐塔納曾設想“藝術的終結”,皮斯特萊托則以創作期冀人類文明的新階段。在2025年,我們應如何解讀他們各自的理想主義?您是如何理解和想象“烏托邦”一詞的?A:在他們的藝術中,我看到的是對未來可能性的展望,這種展望積極而充滿能量。對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未竟之事的探索,使兩位藝術家的理想主義得以具象化。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不僅是一個基金會,更是一個賦能的平臺,在這里,他與年輕的藝術家和創作者們慷慨地分享自己對于美好世界的愿景。他的信念——藝術的力量——似乎始終居于這一實驗性的共享空間的中心。
凡注明 “卓克藝術網” 字樣的視頻、圖片或文字內容均屬于本網站專稿,如需轉載圖片請保留“卓克藝術網”水印,轉載文字內容請注明來源卓克藝術網,否則本網站將依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維護網絡知識產權。

掃描二維碼
手機瀏覽本頁

卓克藝術APP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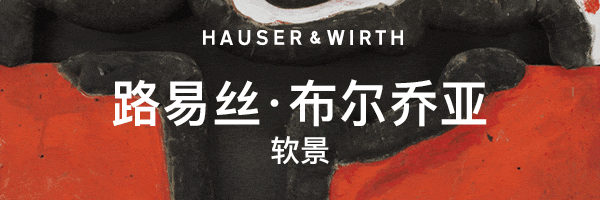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人像》,1962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人像》,1962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碎布墻》,1968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Michelangelo Pistoletto,《碎布墻》,1968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從左到右:Michelangelo Pistoletto,《墻的另一面》,2024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自然》1959-1960年,私人收藏
“鏡像:Lucio Fontana與Michelangelo Pistoletto”展覽現場,上海Prada榮宅,攝影:Alessandro Wang,由Prada提供。從左到右:Michelangelo Pistoletto,《墻的另一面》,2024年,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皮斯特萊托藝術之城基金會,比耶拉;常青畫廊;Lucio Fontana,《空間概念:自然》1959-1960年,私人收藏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