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Ming Dynasty, Zou Dezhong’s Compilation of Painting Things and Pointing To Enlightenment is the first known traditional figure painting book containing “18 etc. of ancient and modern depictions”. These “Eighteen Strokes” are the summaries of the line drawing techniques of the charac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 the Yuan Dynasty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by Zou Dezhong, referred to as “Eighteen Strokes”. Later, after the continuous add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ighteen Strokes” type of painting spectrum evolved into a three-in-one style consisting of the description name, the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pectrum schem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heological changes of the “Eighteen Strok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us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method, and tries to clearly establish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such paintings, aiming to reveal how the names of “Strok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scriptions, and patterns have changed.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y “Eighteen Strokes” class paintings; rheological; evid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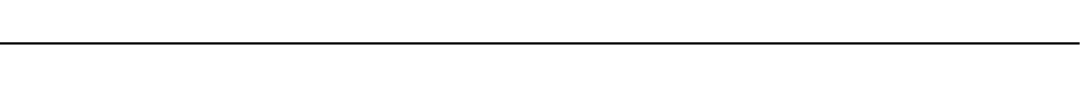
“十八描”是中國傳統人物畫衣褶技法的總括。明清“十八描”類畫譜薪盡火傳之畫論、畫訣、譜列圖式是學習傳統人物畫的指蒙書籍,按四部分類法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此類畫譜在繼承、發展、演進的過程中仍存在諸多懸而未決之問題。故此,本文以歷史文獻法對其進行考證。
鄒德中(生卒年不詳),明代淄川(今約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人,號靜存處士。在淄川縣志及美術史料中,均未有鄒德中生平的記述。他編次的《繪事指蒙》,是目前已知第一部載有“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圖1)的傳統人物畫譜。王世襄于20世紀40年代曾對《繪事指蒙》的版本做過如下研究:“明鄒德中編的《繪事指蒙》,是一部傳本絕少的書。余紹宋先生《書畫書錄解題》列于未見類。最近出版的兩種畫學書目,編者似乎也未見原書。據目前所知,此書全國只有三部,兩個不同的版本;(一)明洪楩刊本。書首署名兩行:‘淄川靜存居士鄒德中編次’。錢塘方泉道人洪楩校刊。卷末有‘成化癸巳東原記’一行七字。書中缺第三十七、四十兩頁,第三十六、四十一兩頁下半截。張珩先生藏。(二)明胡文煥刊本。書首署名前行與洪本同,次行易為:‘錢塘全庵道人胡文煥校正。’卷末無‘東原記’等七字。北京大學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各藏一部。兩個版本行款不同,文字也略有出入。”〔1〕明代洪楩校刊《繪事指蒙》為坊刻單行本,卷尾有明代杜瓊題《東原記》。明代胡文煥刊本《繪事指蒙》為坊刻類書本,列于《百名家書》的第七十二種。
圖1 [明] 鄒德中編次、王世襄校點《繪事指蒙》,“描法古今一十八等”,中國書店1959年版,第六頁右
(一)早于“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總括的兩種衣褶勾描體法“曹吳二體”,是中國古代畫論專述兩種不同風格的人物畫衣褶勾描體法。對“曹吳二體”的記載源于北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志》卷一《論曹吳體法》,總計兩處。第一處直引為:“曹吳二體,學者取宗。按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為曹。謂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后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2〕第二處直引為:“又按蜀僧仁顯《廣畫新集》言曹曰:‘昔竺乾有康僧會者,初入吳,設像行道。時曹不興見西國佛畫儀范寫之,故天下盛傳曹也。’又言:‘吳者起于宋之吳暕之作,故號吳也。’”〔3〕蜀沙門僧仁顯撰《廣畫新集》,目前已很難見到。但是,唐代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有明代王世貞輯《王氏畫苑》本、明代毛晉撰《津逮秘書》本、清代張海鵬輯《學津討原》本等流傳于世。現存《歷代名畫記》諸版本僅記載了曹仲達與吳道子的生平,未有用筆法的詳盡記述。可見,郭若虛的引證文獻并不能言之鑿鑿。《論曹吳體法》引南齊謝赫著《古畫品錄》來駁斥“曹不興、吳暕”一說,以證張彥遠不容置疑的觀點,直引為:“且南齊謝赫云:‘不興之跡,代不復見,唯秘閣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擅名不虛。’吳暕之說,聲微跡曖,世不復傳。至如仲達見北齊之朝,距唐不遠。道子顯開元之后,繪像仍存,證近代之師承,合當時之體范。況唐室已上,未立曹吳,豈顯釋寡要之談,亂愛賓不刊之論。推時驗跡,無愧斯言也”〔4〕。自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起,“曹吳二體”逐漸演變成一說為“曹不興、吳道子”,另一說為“曹仲達、吳道子”。元代湯垕撰《古今畫鑒》沿用“曹不興、吳道子”之說。明代鄒德中編次《繪事指蒙》載“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第九描曹衣描對應曹不興,第十三描柳葉描對應吳道子。中國古代畫論載有四種線描法早于鄒德中總括的“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分別是游絲描、戰筆、行云流水、減筆。游絲描可追溯至南宋趙希鵠撰《洞天清祿集》。鄒德中編次《繪事指蒙》時,在“游絲”前加“高古”,取名高古游絲描,列“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第一位。《洞天清祿集》所載游絲描總計兩處,是辯論前代名家畫人物之專用筆法。第一處直引為:“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褶宛轉曲盡過于李。”〔5〕孫知微是五代后蜀至北宋初年的畫家。元代夏文彥撰《圖繪寶鑒》載:“孫知微,字太古,眉陽彭山人,世本田家,天機穎悟,善畫。初非學而能,清凈寡欲,飄飄然真神仙中人。喜畫道釋用筆放逸,不蹈襲前人筆墨畦畛,時輩稱服,描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6〕孫知微擅畫道、釋,用游絲描畫人物,飄逸不羈,用線精妙不因循守舊,當時的同行稱他用線蒼古,就連同時期的繪畫大家黃筌也不能企及。從上文可知,孫知微畫人物所用線描法特點為細長綿軟,衣褶宛轉曲盡勝過李公麟。第二處直引為:“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尚時省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7〕按上述可知,李公麟和孫太古皆擅以游絲描畫人物,但是二人的線描風格卻差別很大。乃至有元,畫論以“春蠶吐絲”形容顧愷之筆下細長勁韌的用線風格,后面不加“描”字。例如,元代湯垕撰《古今畫鑒》載:“顧愷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8〕迨至有明,書畫類書延續元人記述某朝之某家畫人物用線似春蠶吐絲,非特指顧愷之一人。明代汪砢玉輯《珊瑚網》記有西蜀貫休作《應真高僧像》總計十幅,題名分別為:《達摩》《志公》《言法華》《長汀老子》《普化禪師》《寒山拾得》《善導和尚》《泉太道》《金華圣者》《蝦子和尚》。卷尾附明代李日華跋:“面目手腕描法如春蠶吐絲,衣折用玉箸篆也。王子才亦參禪有得者,又跋:‘梵隆十散圣,衣紋用水荇描法氣韻古澹,余最喜其頌金華圣者云。’”〔9〕李日華引南宋王英孫卷尾跋,敘西蜀貫休作此卷時用線精細,如同春蠶吐絲般連綿不絕,衣褶用秦代李斯玉箸篆筆法,其跡千回百轉,古體遒勁。清代迮朗在前人對游絲描釋義基礎上新增為:“游絲描者,尖筆遒勁,宛若曹衣,最高古也。”〔10〕按上述對游絲描的列舉可知,此描法在歷代傳承中最為古老,因此鄒德中將其列于“描法古今一十八等”之首。顫筆,又作“戰筆”,亦稱“金錯刀”,是古代書論解釋書法用筆的術語。此筆法可追溯至唐代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第八卷,記隋代畫家鄭法士之孫鄭尚子畫人物所用筆法,僅有“善為戰筆之體法甚有氣力”的只言片語。北宋官修《宣和畫譜》是最早記錄此筆法的畫譜,總計三處。第一處直引為,“鄭法士不知何許人也,在周為大都督、員外侍郎、建中將軍,入隋授中散大夫,善畫,師張僧繇。當時已稱高弟,其后得名益著,尤長于人物。至冠瓔佩帶無不有法,而儀矩豐度取像其人。雖流水浮云率無定態,筆端之妙亦能形容。論者謂:‘江左自僧繇已降,法士獨步焉。’法士弟法輪亦以畫稱,雖精密有余而不近師匠,以此失之。子德文、孫尚子,皆傳家學。尚子睦州建德尉,尤工鬼神。論者謂:‘優劣在父祖之間,又善為顫筆見于衣服、手足、木葉、川流者,皆勢若顫動,此蓋深得法士遺范。應之于心者然耳,故他人欲學,莫能仿佛’”〔11〕。第二處直引為:“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也,事偽主李煜為翰林待詔,善畫,行筆瘦硬戰掣,有煜書法。工道釋、人物、車服、樓觀、山林、泉石,不墮曹吳之習而成一家之學,獨士女近類周昉而纖麗過之。”〔12〕第三處直引為:“江南偽主李煜,字重光。政事之暇,寓意于丹青,頗到妙處。自稱鐘峰隱居,又略其言曰鐘隱,后人遂與鐘隱畫混淆稱之。然李氏能文善書畫,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亦清爽不凡別為一格。”〔13〕由上述可知,師從南梁張僧繇的隋代畫家鄭法士、鄭法輪及他們的子嗣在畫人物時用線遒勁,擅用澀勢行顫筆之法。南唐畫家周文矩筆下的人物線條瘦硬,行戰掣之法。南唐后主李煜的書法一筆三折其鋒,落筆藏鋒為一折,提筆轉鋒衄挫為二折,回鋒收筆為三折,他將書法用筆引入到繪畫創作之中。鄒德中將顫筆更為“戰筆水紋描”,列于“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第十五位。元代夏文彥在《圖繪寶鑒》中專述北宋李公麟畫人物筆法擅正鋒轉側鋒,有起有倒,飄然似行云流水。“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城人,登進士第。博覽法書名畫,故悟古人用筆意作書,有晉宋風格。繪事集顧、陸、張、吳及前世名手,所善以為己有專為一家。作畫多不設色,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云行水流有起倒。論者謂:‘鞍馬逾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瀟如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官至朝奉郎。”〔14〕鄒德中將其列于“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第四位,但未給出相應的描法釋義。夏文彥在《圖繪寶鑒》中專述南宋梁楷畫人物的率意筆法,稱為減筆。“梁楷東平相義之后。善畫人物、山水、道釋、鬼神,師賈師古,描寫飄逸青過于藍,嘉泰年畫院待詔,賜金帶楷不受掛于院內,嗜酒自樂號曰梁風子。院人見其精妙之筆無不敬伏。但傳于世者皆草草,謂之減筆。”〔15〕梁楷在畫人物時用筆率意,線條粗獷精簡卻不失法度,世稱減筆。稍早于梁楷的南宋畫家馬遠,在處理山水畫的中遠景人物時也用減筆。因此,鄒德中將此描法的代表畫家釋為“馬遠、梁楷之類”,將其列于“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第十六位。《繪事指蒙》成書時,鄒德中并未給出各種描法的詳盡釋義及譜列圖式。“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描名與描法釋義,如下表(表1)所示。
表1 “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描名與描法釋義表〔16〕二、明代周履靖輯《天形道貌》
周履靖(1549—1640),明代秀水(亦作繡水,今約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人,字逸之,號梅墟、螺冠子、梅癲等。明代萬歷二十六年(1598),周履靖廣搜歷代小種書輯成的類書《夷門廣牘》付梓刊畢。他在自序中稱此書初刻本共十三類,分別為:藝苑、博雅、尊生、書法、畫藪、食品、娛樂、雜占、禽獸、草木、招隱、閑適、觴詠。《夷門廣牘》收錄書目一百零七種,總計一百五十八卷。清代官修《四庫全書》子部收錄《夷門廣牘》十類,書目八十六種,總計一百二十六卷,歸為雜家類,未錄尊生、書法、畫藪。194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涵芬樓藏金陵荊山書林版《夷門廣牘》發行。畫藪是專論畫學的輯錄,計七種十卷,分別為:《畫評會海》為二卷本專論山水、石、樹的畫法集,另附《唐名公山水訣》一卷;《天形道貌》為一卷本人物畫譜;《淇園肖影》為二卷本竹譜;《羅浮幻質》為一卷本梅譜;《九畹遺容》為一卷本蘭譜;《春谷嚶翔》為一卷本翎毛譜;《繪林題識》為一卷本文士題跋。《天形道貌》載有《畫人物論》一篇,鐫“嘉禾周履靖著,茂苑文嘉校正”〔17〕。《畫人物論》篇首文字節錄于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蘇軾為史全叔藏吳道子畫作所作的跋《書吳道子畫后》。此論余下文字分別節錄于唐代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北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志》。《畫人物論》總計一千七百余字,一是論“曹吳二體,學者取宗”。二是論書畫用筆之間的關系,如“畫人物、畫衣紋,用筆全類于書,貴乎筆力”。又如“學畫者要知其描法。如學寫字,先楷而后草也”。三是論畫人物面貌要鮮明,列舉道、釋、儒、帝王、武士、侍女等。四是論人物衣褶的取法、著色、暈染等,如“衣折所貴順適簡暢,最忌繁亂鄙俗,要當師于一人之法足矣”。又如“著色、描法其紋用肥,又要影見。顏色解要濃染,斡要淡開,解又要細”。五是錄一十八種人物衣褶描法。六是論畫人物面像、手足、身體并分別列舉。〔18〕(二)“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與“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差異比對《畫人物論》載“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是錄自鄒德中編次《繪事指蒙》載“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并更正了描法釋義存在訛文的問題。此外,所錄描名、順序也與“描法古今一十八等”有異。“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第八描“撅頭釘”在“描法古今一十八等”作“撅頭丁”。“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第十五描“枯柴描”在“描法古今一 十八等”作“柴筆描”。“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第十一描“柳葉描”在“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原列第十三。“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第十二描“竹葉描”在“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原列第十四。“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第十三描“戰筆水紋描”在“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原列第十五。“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第十六描“蚯蚓描”在“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原列于最后。“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第十七描“橄欖描”在“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原列第十一。“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第十八描“棗核描”在“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原列第十二。“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與“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差異比對,如下表(表2)所示。
表2 “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與“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差異比對表(三)《天行道貌》的譜列圖式
《天行道貌》所載三十六種譜列圖式的題名分別為:《鼓桐》《臨流》《索句》《聽泉》《舞袖》《揮扇》《倚樹》《徜徉》《濯足》《憑石》《趺坐》《散步》《醉吟》《傳杯》《采芝》《攜琴》《題壁》《觀水》《回首》《靜憩》《晤語》《觀泉》《談玄》《浮白》《觀書》《拂塵》《望月》《呼童》《酕醄》《酩酊》《讓履》《盤桓》《倦繡》《調鸚》《搗衣》《題葉》。另附四幅《寫意》圖式,譜列圖式總計四十幅。除四幅《寫意》圖式為意筆法勾勒外,其余三十六幅圖式均為細線勾勒。三、明代楊爾曾輯《圖繪宗彝》
楊爾曾(?—約1612),明代武林(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字圣魯,號雉衡山人、夷白道人。明代萬歷三十五年(1607),楊爾曾輯《圖繪宗彝》由蔡汝佐繪,黃德寵鐫于武林。本文所擇《圖繪宗彝》現庋藏于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歸中國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畫譜編號T6130/4218,入館時間為1954年6月24日。《圖繪宗彝》分為上下兩冊,總八卷;題簽為“圖繪宗彝”,書名頁鐫“武林楊衙夷白堂精刻不許番刻”(圖2),右上角鈐朱文印“奇賞”;白口,四周單邊框,版心鐫卷數。《敘圖繪宗彝》(圖3)篇首鈐朱文印“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篇尾鐫“時萬歷丁未秋仲之,老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題”,鐫陰文印“楊爾曾印”、鐫陽文印“字圣魯”,鐫“新安沖寰蔡汝佐繪,玉林黃德寵鐫”。此畫譜第一卷是先圖而后論,第六卷無論、無訣,僅刻譜列圖式,其余各卷體例為畫論加譜列圖式的形式。
圖2 [明] 楊爾曾輯、蔡汝佐繪、黃德寵鐫《圖繪宗彝》上冊卷一,書名頁,鈐朱文印“奇賞”、鐫“武林楊衙夷白堂精刻不許番刻”,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武林夷白堂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圖3 [明] 楊爾曾輯、蔡汝佐繪、黃德寵鐫《圖繪宗彝》上冊卷一,《敘圖繪宗彝》,鈐朱文印“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武林夷白堂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圖繪宗彝》上冊卷一專論人物畫技法與山水畫技法,鐫人物譜列圖式四十二幅,另附寫意二幅,總計四十四幅。楊爾曾輯《圖繪宗彝》上冊卷一載《畫人物論》出自周履靖輯《天行道貌》,故不作贅述。按《圖繪宗彝》上冊卷一目錄順序,譜列圖式的題名分別為:“《普門示現》《波斯洗象》《文章司命》《達摩折蘆葉渡江》《三教圖》《松巖伏虎》《鼓桐》《臨流濯足》《聽名泉》《觀書》《徜徉》《揮毫》《攜琴》《索句》《憑石》《揮扇》《倚樹》《傳杯》《酩酊》《望月》《梧桐》《談玄》《回首》《提筆》《讓履》《呼童》《搗衣》《舞袖》《倦繡》《題葉》《調鸚鵡》《玉兔秋香》《春江水漲》《蹇驢踏雪》《遠浦歸帆》《江天暮色》《漁舟暢飲》《田夫牽牛》《農家扇米》《鐘馗跨鹿》《耕牛引犢》《披蓑牽網》《寫意》。”〔19〕《圖繪宗彝》上冊卷一目錄頁所記譜列圖式與卷中所載譜列圖式在順序及題名上有一定的出入。譜列圖式《普門示現》(圖4)、《波斯洗象》《三教圖》《松巖伏虎》又見于明代萬歷三十一年(1603)顧炳輯《歷代名公畫譜》之內。上述兩種畫譜所載之四幅譜列圖式除《普門示現》外,其余三幅譜列圖式并無較大異同。
圖4 [明] 楊爾曾輯、蔡汝佐繪、黃德寵鐫《圖繪宗彝》上冊卷一,譜列圖式《普門示現》,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武林夷白堂版,第五頁左,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圖繪宗彝》上冊卷一載《普門示現》與《顧氏畫譜》第一冊載唐代吳道子繪《普門示現》(圖5)的差別有如下四點。首先,《圖繪宗彝》所載《普門示現》的觀音像有頭光、髻珠、化佛,此像“眉間放白毫,光照見東方十萬億國土,皆在座下以聽說法,是天竺以東無一國不在其法會矣”〔20〕;《顧氏畫譜》所載《普門示現》的觀音像無白毫。其次,《圖繪宗彝》所載《普門示現》觀音像的發絲是細筆勾勒,分列兩端的發絲清晰可見;《顧氏畫譜》所載《普門示現》的觀音像自化佛開始無兩端之精細發絲。再次,《圖繪宗彝》所載《普門示現》的觀音像胸前正中間繪有“卍”字,為觀音“三十三身十九說法的第一像‘佛身像’”〔21〕;《顧氏畫譜》所載《普門示現》的觀音像胸前正中間未繪有“卍”字。最后,鸚哥在兩幅《普門示現》中的位置與朝向各不相同。
圖5 [明] 顧炳輯《歷代名公畫譜》第一冊,唐代吳道子《普門示現》,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武林雙桂堂版,圖片來源/吳樹平主編《中國歷代畫譜匯編》第一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頁
(二)《圖繪宗彝》上冊卷一譜列圖式題名與《天行道貌》譜列圖式題名的差異比對《圖繪宗彝》上冊卷一譜列圖式題名與《天行道貌》譜列圖式題名的差異比對,如表3所示。
表3《圖繪宗彝》上冊卷一譜列圖式題名與《天行道貌》譜列圖式題名的差異對比表四、明代汪砢玉輯《珊瑚網》
汪砢玉(1586—1646),明代秀水(亦作繡水,今約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人,原籍明代徽州(今約安徽省黃山市徽州區),因科舉寄籍嘉興,一作珂玉,字玉水,號樂卿、樂閑外史,崇禎年間任山東鹽運使判官。1916年,上海國學扶輪社版,張鈞衡編《適園叢書》所錄明代汪砢玉輯《珊瑚網》,是他按清代乾隆至嘉慶年間錢塘著名藏書家何夢華藏本,再借嘉惠齋本輯校而成。張鈞衡輯校本《珊瑚網》后記曰:“《珊瑚網》四十八卷,汪砢玉玉水撰。玉水徽州人,寄籍嘉興。崇禎中,官山東鹽運使判官。是書成于崇禎癸未末,凡法書題跋二十四卷,名畫題跋二十四卷。《靜志居詩話》稱玉水留心著述。所輯《珊瑚網》一編與張丑《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錄》并駕。蓋丑自其高祖以下四世見藏。玉水亦以其父愛荊與嘉興項元汴交好,筑凝霞閣以貯書畫。收藏之富甲于一時,其有所憑借約略相等。故皆能搜羅薈萃勒為巨編。前列題跋,后附論說,綱領節目,秩序有條致所有。后來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厲鶚《南宋畫院錄》皆籍是書以成。較在書跋之上,向無刻本,輾轉傳抄,時多駁誤。先得一鈔本,訛脫極多。后得何夢華藏本,字跡極雅,校亦甚精,惜文殘缺,復假嘉惠齋舊鈔本補足。三本合校,尚未能全行是正,惟盼后人匡我不逮。第脫葉錯簡,大半改正矣。歲在柔兆執徐。吳興張鈞衡跋。”〔22〕汪砢玉輯《珊瑚網》,是明代書畫著錄的類書,分上下兩部分,計四十八卷。此書前二十四卷為古今法書,總序為《汪氏珊瑚網古今法書題跋敘》落“崇禎癸未天中節,攜李玉水汪砢玉樂卿氏識于東雅堂左隅之漱六齋”〔23〕,記載了曹魏時期鐘繇以后的法書真跡、款識、叢拓等。此書后二十四卷為古今名畫,總序為《汪氏珊瑚網古今名畫題跋敘》落“崇禎癸未嘉平臘,繡水汪砢玉樂卿甫識于墨花閣右之韻石齋”〔24〕,記載了晉代顧愷之所遺真跡至明代麟湖沈氏墨林所藏畫目,又將唐代張彥遠,宋代蘇軾、米芾、鄧椿等人的著錄一并編入。《汪氏珊瑚網畫法》附二十四卷后《諸名家繪法纂要》,是汪砢玉以鄒德中編次《繪事指蒙》為參本輯成的。他剔除了鄒德中總結的“勾勒”“著色”“暈染”等畫工技法,取而代之的是文人畫水墨技法。《諸名家繪法纂要》與《繪事指蒙》的差異比對,如表4所示。
《汪氏珊瑚網畫法》附二十四卷后《諸名家繪法纂要》,更《繪事指蒙》“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為“古今描法一十八等”,另增馬蝗描一名為蘭葉描。蘭葉描在后世書畫類書中廣泛流傳,進而混亂地成為“十八描”以外的新描名。明清“十八描”類畫譜東傳日本后,明治時代畫家久保田米仙(1852—1906)在編撰《畫法大意》時,甚至將蘭葉描新增為第十九種描法。由于編撰者增刪導致描法釋義的畸變,遂成為此類畫譜在傳承與傳播過程中突出存在的問題。筆者在詳細耙梳《珊瑚網》有關馬蝗描的記述時發現,此書共兩次提及馬蝗描。《珊瑚網》卷十九載《漱六齋六法英華》,是汪砢玉集攬唐、宋、元歷代真跡共二十冊的甲級藏品。他在敘述第十三幅絹橫批《干旄圖》時提及了馬蝗描,直引為:“孑孑干旄建于車后,兩服兩驂而維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彼姝者,子罄折且前,是欲以畀之氣象耳,衣折作馬蝗描。古法昭燦,如睹商周法物。樂卿。”〔25〕他第二次提及馬蝗描釋義是在《汪氏珊瑚網畫法》附二十四卷后《諸名家繪法纂要》,直引為:“馬和之、顧興裔之類,一名蘭葉描。”〔26〕“馬和之蘭葉描出于吳道子”一說,可追溯至明代何良俊撰《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九,直引為:“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于李龍眠,李龍眠出于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27〕汪砢玉在轉錄“描法古今一十八等”馬蝗描釋義時增“一名蘭葉描”,他的臆測造成后世轉錄明刻本的書畫類編在描名和釋義上存在混亂與歧義且愈演愈烈。“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第五描馬蝗描的釋義為“馬和之、顧興裔之類”,是指南宋錢塘畫家馬和之及其學生顧興裔畫人物衣褶的專有筆法。元代湯垕撰《古今畫鑒》載:“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為小吳生。更能脫去俗習,留意高古,人未易到也。”〔28〕上溯至唐代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朱景玄撰《唐朝名畫錄》,北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志》、官修《宣和畫譜》,元代夏文彥撰《圖繪寶鑒》、湯垕撰《古今畫鑒》有關吳道子條目,筆者均未見“蘭葉描”一說。除此之外,在唐代至元代諸家以繪畫鑒藏為目的所撰之畫評、補遺、續編、瑣錄、畫跋之中,也未見此說。寫蘭葉之法在明清花鳥畫譜中十分常見,各家蘭譜多有文字記述和譜列圖式。明代周履靖輯《九畹遺容》為蘭譜。“九畹”典出戰國末期楚國屈原作《離騷》,后世用它指代蘭花。《九畹遺容》載有周履靖輯《寫蘭訣》一篇,直引寫蘭葉法為:“寫蘭之妙,氣韻為先。墨須精品,水必新泉。硯滌宿垢,筆純忌堅。先分四葉,長短為玄。一葉交搭,取媚取妍。各交葉畔,一葉仍添。三中四簇,兩葉增全。墨須二色,老嫩盤旋。”〔29〕此訣以寫蘭葉程式為開端,再論用筆、用墨,寫蘭花頭、花萼等程式。清代王概、王蓍、王臬撰繪《芥子園畫譜》二集卷一《蘭譜》有對寫蘭葉線條樣式的描述,直引為:“或粗如螳螂肚或細如鼠尾。”〔30〕寫蘭葉程式在明清蘭譜中,多以藏鋒筆法為主,多見書法捺畫的波折筆。寫蘭葉的用筆順序是正鋒藏鋒起手,行筆有停頓、有躍筆提行,收筆為虛,不益過尖。清代汪之元撰繪《天下有山堂畫藝》卷一是蘭譜。此譜成書于清代雍正二年(1724),初刻本為四明樵石山房版,由圖里琛作序,落“雍正二年甲辰嘉平月,睡心主人圖里琛拜手書于粵藩官屬之來鶴亭”〔31〕。本文擇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字圖書館藏,日本大正六年(1917)晚翠軒影印四明樵石山房版《天下有山堂畫藝》卷一(書志ID為000000580972)載《墨蘭指·附蕙石苔草二十八則》寫蘭葉法十條,另附寫蘭葉譜列圖式四幅(圖6、圖7、圖8、圖9),直引如下。
圖6 [清] 汪之元撰繪《天下有山堂畫藝》卷一,《墨蘭指·附蕙石苔草二十八則》,寫蘭葉譜列圖式一,日本大正六年(1917)晚翠軒影印四明樵石山房藏版,第十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字圖書館藏
圖7 [清] 汪之元撰繪《天下有山堂畫藝》卷一,《墨蘭指·附蕙石苔草二十八則》,寫蘭葉譜列圖式二,日本大正六年(1917)晚翠軒影印四明樵石山房藏版,第十一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字圖書館藏
圖8 [清] 汪之元撰繪《天下有山堂畫藝》卷一,《墨蘭指·附蕙石苔草二十八則》,寫蘭葉譜列圖式三,日本大正六年(1917)晚翠軒影印四明樵石山房藏版,第十二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字圖書館藏圖9 [清] 汪之元撰繪《天下有山堂畫藝》卷一,《墨蘭指·附蕙石苔草二十八則》,寫蘭葉譜列圖式四,日本大正六年(1917)晚翠軒影印四明樵石山房藏版,第十三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字圖書館藏
1.“寫蘭之法,起手只四筆耳。其風韻飄然,不可著半點塵俗氣。叢蘭葉須掩花,花后插葉,亦必疏密得勢,意在筆先。自四葉起至數十葉,少不寒悴,多不糾紛,方為名手。”
2.“寫蘭用筆與寫竹法同,前已言之詳矣。惟葉起自四筆,寫到數叢皆不紛亂者,以有此規矩在于胸中耳。規矩者何?即譜中起手層次交互之法也。”
3.“蘭葉與蕙葉異者,剛、柔、粗、細之別也。粗不似茅,細不類韭,斯為得之!”
4.“寫葉自左而右者順且易,自右而左者逆且難。但先熟習其自右而左,則自左而右者,不習而能矣。必使左右并妙,然后為佳。”
5.“護根乃蘭葉之甲坼也,更宜俯仰得勢,高下有情,簡不疏脫,繁不重疊,然必以少為貴。”
6.“折葉使筆起手時,筆尖微向葉邊,行到轉折處,筆尖居中,向后須以勁取勢。軟而無力,便是草茅,不足觀也。”
7.“葉之剛柔,要在落筆時存心為之。剛非生硬,柔避軟弱,在人能體會其意。”
8.“兩叢交互,須知有賓主,有照應。”
9.“寫蘭難在葉,寫蕙葉與花俱難,且安頓要妥,若一箭有不適然,便無生意。且葉有好處,不可以花遮掩,有不好處,即以花叢勝于其間,便成全美矣。”
10.“用筆雖同寫竹,必先在于得勢。長、短、高、下,安頓得宜。落筆未發,須避前面交叉。落筆既發,須讓后來余地。花后添插數葉,則叢叢深厚不墮淺薄之病矣。”〔32〕按上述明清蘭譜記載的寫蘭程式可知,寫蘭葉用筆重在起、行、轉、收,行筆過程皆有變化,共性為藏鋒起,行筆衄挫無圭角,線條或粗如螳螂肚或細如鼠尾,收筆為虛,不益過尖。1861年,清代旅日畫家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的馬蝗描釋義為“如馬蝗系”,并附譜列圖式。王贏繪馬蝗描譜列圖式多用折筆,線條似馬蝗緊系狀。1924年,黃澤繪《古佛畫譜》的蘭葉描被歸為釘頭鼠尾描之異名,直引為:“蘭葉描又名釘頭鼠尾描,用細小長鋒筆如畫蘭葉法,所謂釘頭鼠尾螳螂肚是也。”〔33〕由此可見,馬蝗描盤曲緊系的線條樣式與寫蘭葉粗如螳螂肚或細如鼠尾的線條樣式不能混為一談。
鄭績(1813—1874),清代新會(今約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人,字紀常,號戇士,別署夢香園叟。清代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五年(1866),鄭績撰繪《夢幻居學畫簡明》由廣州九曜聚賢堂陸續刊刻。此畫譜總計五卷,卷一專論山水,卷二專論人物,卷三專論花卉,卷四專論翎毛,卷五專論獸畜附鱗蟲。卷首《自序》落“同治甲子上元,鄭績自記”〔34〕,卷尾《總跋》落“同治丙寅歲花朝,紀常鄭績謹跋”〔35〕。此譜每卷先著總論,契為大綱,以述古為證。余下瑣論皆錄前人畫學或經作者心學發揮,簡單明了,使研學之人一目了然。第二卷專論人物,直引《人物總論》為:“寫山水點景人物,以山水為主,人物為配。寫人物補景山水,則以人物為主,山水為配。此論主在人物畫也。而畫人物有工筆、意筆、逸筆之分。工筆、意筆、逸筆之中又有流云法、折釵法、旋韭法、淡描法、釘頭鼠尾,各家法不同。如用某家筆法寫人物,須用某家筆法寫樹石配之,不能夾雜。世有寫眉目、須發用工筆,而冠履、衣紋用意筆。又以工筆寫人物而用意筆寫樹石。一幅兩家,殊不合法,此近俗。流弊因訛傳訛,往往習而不察,有志畫學者當分辨之。”〔36〕目次分別為:《人物總論》(一條),《人物述古》(二條),《論工筆》(六條),《論意筆》(四條),《論逸筆》(三條),《論尺度》(三條),《論點睛》(二條),《論肖品》(五條),總計八篇二十六條。《續卷二》附人物總譜,含《白云山市圖》長卷在內,總計二十四幅譜列圖式。《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專論人物的篇章分別節錄于北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志》、官修《宣和畫譜》。《論工筆》《論意筆》《論逸筆》是述論前人衣褶畫法的若干條,并附譜列圖式。除錄前人一種描法外,另增四種變異描法,分別為流云法、折釵法、旋韭法、淡描法。按《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載畫人物衣褶流云法,直引為:“流云法,如云在空中旋轉流行也。用筆長韌,行筆宜圓,人身屈伸,衣紋飄曳,如浮云舒卷故取法之。其法與山石云頭皴同義。寫炎暑秋涼單紗薄羅,則衣紋隨身緊貼。若冬雪嚴寒重裘厚襖,則衣紋離體闊折,宜活寫之。”〔37〕再按《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一載《十六家皴法》,直引為:“皴分十六家:曰披麻、曰云頭、曰芝麻、曰亂麻、曰折帶、曰馬牙、曰斧劈、曰雨點、曰彈渦、曰骷髏、曰礬頭、曰荷葉、曰牛毛、曰解索、曰鬼皮、曰亂柴。此十六家擦法即十六樣山石名目,并非杜撰。至每家皴法中又有濕筆焦墨,或繁或簡,或擦或不擦之分。不可固執成法必定如是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38〕鄭績所言十六家皴法與明代鄒德中編次《繪事指蒙》載《石名》、明代汪砢玉輯《汪氏珊瑚網畫法》附二十四卷后《諸名家繪法纂要》載《寫石二十六種》相似,唯順序和數目有異。鄭績對云頭皴的釋義有二則,第一則直引為:“云頭多主筋。馬牙、亂柴多主骨。而披麻、云頭亦有主骨者。馬牙、亂柴亦有主筋者。余可類推,皆不能固執一定。總由用筆剛柔,隨意生變,欲筋則筋愛,骨則骨耳”〔39〕。第二則直引為:“云頭皴如云旋頭髻也。用筆宜干,運腕宜圓,力貫筆尖,松秀長韌,筆筆有筋,細而有力。”〔40〕《夢幻居畫學簡明》所載人物衣褶流云法與山石皴法云頭皴,在用筆上的描述十分相近。雖然流云法在前人畫譜中未見其名,按鄭績所言屬北宋李公麟行云流水描一脈,主正鋒轉側鋒,行筆有起有倒。鄭績在流云法釋義中還強調,因時制宜地區分人物夏季和冬季所著不同質地的服裝,進而呈現衣褶上的隨身緊貼與離體闊折。《夢幻居畫學簡明》續卷二《人物總譜》附流云法譜列圖式三幅,題名分別為:《奇文共賞》《擲杖化龍》《濯足扶桑》。按《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載畫人物衣褶折釵法,直引為:“折釵法如金釵折斷也。用筆剛勁,力趨鉤踢,一起一止,急行急收。如山石中亂柴、亂麻、荷葉諸皴,大同小異,像人身新衣膠漿折生棱角也。”〔41〕折釵法源于折釵股。折釵股,又名“古釵腳”,是形容書家筆力遒勁之義,多見于歷代書論。按北宋周越纂《古今法書苑》載:“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于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腳對。”〔42〕又按南宋姜夔撰《續書譜》載:“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后人之論。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欲其無起止之跡。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43〕鄭績用書學折釵股對釋畫學折釵法。書學折釵股用筆有正偃之分。畫學折釵法用筆有力趨鉤踢,折生棱角之分,寫線一波三折,轉折處見圭角。畫學折釵法貴在人物肢體處見衣紋之轉折,似蚯蚓描用藏鋒起手,行筆到人物衣褶轉折處時又似鐵線描。《夢幻居畫學簡明》續卷二《人物總譜》附折釵法譜列圖式二幅,題名分別為:《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一奴長須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按《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載畫人物衣褶旋韭法,直引為:“旋韭法如韭菜之葉旋轉成團也。韭菜葉長細而軟,旋回轉折取以為法,與流云同類。但流云用筆如鶴嘴畫沙,圓轉流行而已。旋韭用筆輕重跌宕,于大圓轉中多少攣曲,如韭菜扁葉悠揚輾轉之狀,類山石皴法之云頭兼解索也。然解索之攣曲,筆筆層疊交搭。旋韭之攣曲,筆筆分開玲瓏。解索筆多干瘦,旋韭筆宜肥潤,尤當細辨。李公麟、吳道子每畫之。”〔44〕鄭績用鶴嘴畫沙和解鎖皴來釋義流云法,以便與旋韭法進行區分。鶴嘴畫沙,又作“鶴嘴劃沙”,是用來形容元代王蒙開創的解索皴筆法。此法最早見于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布顏圖撰《畫學心法問答》載元四家畫法異同,直引為:“問元代黃、王、倪、吳四家畫法有以異乎?曰:‘四家皆師法北宋,筆墨相同而各有變異。子久師法北苑,汰其繁皴瘦其形體,巒頂山根重如疊石,橫起平坡自成一體。王叔明號黃鶴山樵,松雪之甥也,少學其舅,晚法北苑。將北苑之技麻皴屈律其筆,名為解索皴。其堅硬如金鉆鏤石,利捷如鶴嘴劃沙,亦自成一體。”〔45〕鶴嘴劃沙自布顏圖始,未見于歷代書論與畫論。錐畫沙,又作“錐沙”,多見于歷代書論之中。“唐褚遂良《論書》載:‘用筆當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宋黃庭堅《書扇》詩:‘魯公筆法屋漏雨,未滅右軍錐畫沙。’宋姜夔《續書譜》:‘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46〕鄭績將旋韭法歸為吳道子和李公麟一脈。此描法注重轉折回旋,輕重緩急,多小攣曲,似山水解索皴。旋韭法與解索皴不同之處在于用筆玲瓏精細,墨色肥潤。吳道子擅柳葉描,畫觀音像用棗核描,他筆下人物衣褶的線條特征為莼菜狀。按布顏圖所言,趙孟頫畫人物衣褶追法李公麟,其子趙雍的書畫繼承家學,其外孫王蒙早年追法趙雍后學五代董源。然而,吳道子、董源、李公麟、趙雍、王蒙筆下線條在歷代畫論中均未見韭葉狀的記述。《夢幻居畫學簡明》續卷二《人物總譜》附旋韭法譜列圖式二幅,題名分別為:《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不食五谷啖百華》。按《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載畫人物衣褶淡描法,直引為:“淡描法,輕淡描摹也,用筆宜輕,用墨宜淡。兩頭尖而中間大,中間重而兩頭輕。細軟幼致,一片恬靜,裊娜意態,故寫仕女衣紋此法為至當。”〔47〕鄭績將淡描法用筆釋為兩頭尖中間大,中間重兩頭輕。按上述釋義可知,用淡描法寫出的線條特征為兩頭細尖無波折,其墨色特征為兩端稍淡中間稍重。《夢幻居畫學簡明》續卷二《人物總譜》附淡描法譜列圖式二幅,題名分別為:《明月歸路影婆娑》《浴乎沂風乎舞雩》。
王贏(1785—1862),浙江杭縣(今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人,字海仙、良平、百谷、百合,號巨海,清代旅日書畫家。王贏旅居日本京都期間的曾用名有小田海仙、小田良平、小田贏、小田百谷等。按日本天保二年(1831)白井華陽撰《畫乘要略》載,“小田百谷,名贏字巨海,百谷其號,又號海仙,長門人來居平安。初學月溪,后舍舊習,效元格擅山水、工人物、花鳥,又長臨摹。北汀先生曰:‘海仙厭其師月溪,專新奇。東奔西走,多摹元明之古跡。辛苦百方,遂變師傳。于其山水清疏澹蕩,秀逸膏潤,人扱稱其能’”〔48〕。王贏擅畫山水、人物、花鳥,人物畫作品有《福祿壽圖》《大槻玄澤肖像》《美人納涼圖》等傳世。他應京都出版商的邀請校對過部分明清畫論。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王贏校對明代董其昌撰、清代汪汝祿編次《畫禪室隨筆》,由東京都錢屋揔四郎刊刻。日本文久元年(1861)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又名《海仙畫譜》,付梓刊畢。此譜現藏于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分類種別為和古書、漢籍(書志ID為000007279869)。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題簽為“海仙十八描法”;書名頁鐫“巨石陳云”,鈐朱文印“風云窟”,題“贈呈志水良三君”,落“陶春植木吉英”,鈐朱文印“陶春”(圖10);版心鐫“海仙畫譜”及篇名,黑魚尾,下鐫“海仙庵藏”,白口,四周單邊框。畫譜有王贏作《自序》、日本幕末著名漢學家齋藤正謙作《拙堂序》,譜列圖式總計十八幅,錄前人《畫人物論》一篇。
圖10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書名頁,鐫“巨石陳云”,鈐朱文印“風云窟”、題“贈呈志水良三君”、落“陶春植木吉英”、鈐朱文印“陶春”,日本文久元年(1861)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顧愷之曰:‘畫道中人物最為難,山水次之’。而人物有衣紋描法十八等,山水亦有峰巒皴法十六等。清王安節既有就諸書,索搜古圖而某皴師某人,某皴之創于某人,皆圖上辨之某審,今時為初學畫山水階梯。余亦仿其意,就古人所論描法,往之索搜古圖,遂成此舉矣。昔吳道子學書于張旭畫大進矣。古人云:‘衣紋用筆全類于書’。由是觀之書與畫同一法也。余因謂寫人物肢體譬如峰巒,衣紋譬如云煙。云煙要變化,而用筆需要如書法。肢體須逼真,而用筆之要存心要恭,落筆要放。存心不恭則下筆藪漫,格法不具。落筆不放易無生動之氣。以恭寫放,以放應恭,始得收放。至今人之畫粗能寫貌,得其形似而俗體橫出,衣紋無法邪說紛起,日遠古人可嘆也!故余著此書為初學南針。各家描法取性相近,習熟自然,心手相應。始識者對之,終日不倦,物我兩忘。至于此六法能事畢矣。果然直臻吳曹堂奧,亦何難之有?故后附書法攜轍,以便初學者臨習之。安政六年歲在已未春三月,洛東錦織邨隱棲海仙王贏識。”〔49〕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之目的在于“以圖辨審”,又參照書學探究描法之本義。“今日殆為絕學。翁獨研究曹吳遺法,以為畫本。書法存六書,以象形居其一,不可不識其本也,因并論及書法。翁又好讀史,衣服、冠冕據史正之,無一杜撰。人多謂:‘翁寫人物在本邦為古今獨步’。想應不誣也。翁今年七十有五,新著十八描法,孜孜從事鈶槧,可謂志篤矣,可謂業勤矣。書已成,索序于余。余不解繪事,然至于畫學之源流,常于書史中得略識之,乃書此為序,以塞責。安政六年歲次屠維協洽春王三月,伊勢拙堂莊士齋藤謙識并書。”〔50〕《海仙十八描法》的描名、描法釋義鐫于譜列圖式之上(圖11、圖12、圖13、圖14、圖15、圖16、圖17、圖18、圖19、圖20),匯總后如表5所示。
圖11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高古游絲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一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2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琴弦描釋義及譜列圖式、鐵線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一頁右至第二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3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行云流水描釋義及譜列圖式、馬蝗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二頁右至第三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4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釘頭鼠尾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混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三頁右至第四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5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撅頭釘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曹衣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四頁右至第五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6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折蘆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柳葉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五頁右至第六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7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竹葉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戰筆水紋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六頁右至第七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8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減筆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枯柴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七頁右至第八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9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蚯蚓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橄欖描釋義及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八頁右至第九頁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20 [清] 王贏撰繪《海仙十八描法》,棗核描釋義及描譜列圖式,日本文久元年(1861)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村海仙庵藏識版,第九頁右,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表5 “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的描名與描法釋義匯總表〔51〕
錬筆,分別出現在高古游絲描和行云流水描的釋義之中。《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釋:“《集韻》籠切。音東。《集韻》:‘或作鍊’又田器,以此推之,則錬為鍊之偽也。”〔52〕《漢語大字典》釋:“錬,‘鍊’的訛字。《正字通·金部》:‘錬為鍊之偽’。清戴震《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又有本無其字,因偽而成字。引《方言》,則鍊偽而為錬,遂與東同音’。”〔53〕錬為鍊(煉)的訛字,但在日制漢字中可互通,按《日語漢字讀音速查詞典》釋“‘鍊’‘練’‘錬’音讀為[レン]”〔54〕,皆為將某物精細化之義。惹筆,分別出現在蚯蚓描和橄欖描的釋義之中。西漢楊雄著《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卷釋:“拏,揚州會稽之語也。或謂之惹,或謂之?。”〔55〕惹筆最早見于南宋徐夢莘編《三朝北盟會編》,直引為,“楊璞,高慶裔來傳尼堪指揮,斥字畫惹筆提拔不謹。對以:‘自來國書止有司分人修寫,拘于體例自無惹筆。今系主上親御翰墨是尊崇大國之意。’慶裔云:‘誓書有不提空并惹筆須著換’。對以:‘此誓書元在闕下,為使人陳乞已換了兩次,到涿州又換一次,敵國往來豈有此理’。慶裔云:‘誓書要傳萬世,親寫故知是厚意。兩國相重書狀往還,寫得真楷是厚意?為復寫得惹筆是厚意?”〔56〕按上述可知,惹筆分別對應“謹”“體例”“真楷”,指金國國書字跡草亂相連之義。惹筆在蚯蚓描和橄欖描釋義中,是取惹之“牽”義,強調行筆時迅速的轉鋒。怒降,分別出現琴弦描、柳葉描和蚯蚓描的釋義之中。怒降,原義寫楷書時運筆過快。按明代張紳撰《法書通釋》錄唐代歐陽詢《八訣》述:“澄心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后。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則傷神采,墨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于軟弱,不得怒降為奇。”〔57〕按明代董其昌書《論書帖》曰:“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強之謂,乃如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58〕筆頭為玉,出現在棗核描的釋義之中。玉,為象形字,字形像一串碧玉,由“|”穿起,古金文寫作“王”。按大徐本《說文解字》釋:“王象三王之連,丨其貫也。”〔59〕“王”“玉”在古金文中的字形十分相似。古金文中“王”的三筆橫畫依書寫次序分別象征著天、人、地,“三才”以丨連起,代表人的第二筆橫畫靠近代表天的第一筆橫畫,取王者法天之義。而“王”(玉)字的三筆橫畫正均分布。玉同王的字形相近,僅在中畫分布位置上有區別。北宋王洙、胡宿、司馬光等在編纂《類篇》時,玉始加點以別王字。筆頭為玉,是突出點畫的用筆地位,強調點畫形狀如同棗核。棗核描用筆特點是藏鋒回筆作“玉”之點狀,轉折處不突出衄挫和圭角,收于虛筆。疾,出現在撅頭釘描的釋義中。波,出現在戰筆水紋描的釋義中。疾與澀是書法的勢。按清代馮武編《書法正傳》引東漢蔡邕作《九勢》言:“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防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獻酧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夫書稟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軟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后自然無師授,而合于先圣矣’。”〔60〕澀勢是顫行,有緊收之力。又按唐代孫過庭書《書譜》載:“一畫之間,變起伏于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于毫芒。”〔61〕衄挫,一作“劍挫”,又作“?挫”,?為衄之異體字。疾與澀間的轉換稱衄挫,即挫折,是筆勢退縮之義。再按南宋陳思撰《書苑菁華》載:“疾勢出于啄磔之中,又在豎筆緊趯之內。澀勢在于緊戰行之。”〔62〕啄是短的撇,下筆駐鋒后即出,書家形容短撇如鳥用喙捕食般有力。磔是捺畫,微直,橫筆為波,兩筆橫捺。波是捺畫的折態,運筆如波狀有曲流之勢,“一波三折”即是此義。緊趯,即緊躍,是寫豎畫須緊張而不松散的一種快態。疾與澀之間的轉換涵蓋了運筆的提、按、頓、挫,更囊括了書法用筆在放與攢之間的對立統一。戰筆水紋描最能展現書法同繪畫之間的緊密關系,體現了傳統人物衣褶描法重視筆法上的起、行、轉、收,凸顯了用筆上的變化與統一。
明清“十八描”類畫譜嚆矢于《繪事指蒙》,集大成于《海仙十八描法》。正是因為明清諸家對此類畫譜不斷地增修,才演進出描法釋義同譜列圖式彼此組合的體例,且描法釋義與譜列圖式可相互印證。首先,此類畫譜的演進過程是遵循從簡單到復雜、由一般到個別的方式來表征描法釋義和譜列圖式之間的聯系。其次,此類畫譜的描法釋義及譜列圖式在流變中凸顯了書畫同源的藝術主張。最后,此類畫譜的描法釋義與譜列圖式,以文本和圖像之間的語圖關系一同詮釋了描名,且二者能夠精煉地、準確地描述出特指畫家之專有筆法,進而形成畫學上的圭臬。(本文為2022年11月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明清‘十八描’類畫譜的流變研究”課題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YSB217)
注釋:
〔1〕王樹村《中國民間畫訣》,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頁。〔2〕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一,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頁。〔3〕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一,第469頁。〔4〕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一,第469頁。〔5〕王云五《叢書集成初編:負暄野錄及其他一種》,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25頁。〔6〕[元] 夏文彥《圖繪寶鑒》卷三,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第33頁。〔7〕王云五《叢書集成初編:負暄野錄及其他一種》,第25頁。〔8〕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冊二,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第894頁。〔9〕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冊五,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6頁。〔10〕王世襄《中國畫論研究》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510頁。〔11〕[宋] 官修《宣和畫譜》卷五,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頁。〔14〕[元] 夏文彥撰《圖繪寶鑒》卷三,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第35頁。〔15〕[元] 夏文彥撰《圖繪寶鑒》卷四,第79頁。〔16〕[明] 鄒德中編次,王世襄校點《繪事指蒙》,中國書店1959年版,第9頁。〔17〕吳樹平《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十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頁。〔18〕吳樹平《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十二,第403—405頁。〔19〕[明] 楊爾曾《圖繪宗彝》卷一,萬歷三十五年武林夷白堂刻本,第4頁。〔20〕王云五《叢書集成初編:庶齋老學叢談及其他兩種》,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6頁。〔21〕[日] 高楠順次郎《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經疏部二》卷三十四,東京都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年版,第79頁。〔22〕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冊五,第1240頁。〔25〕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冊五,第1172頁。〔26〕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冊五,第1238頁。〔27〕[明]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九,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64頁。〔28〕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冊二,第1238頁。〔29〕吳樹平《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十五,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280頁。〔30〕吳樹平《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頁。〔31〕[清] 汪之元《天下有山堂畫藝》卷一,日本晚翠軒1917年影印本,第4頁。〔32〕[清] 汪之元《天下有山堂畫藝》卷一,第6頁。〔33〕黃澤《古佛畫譜》,湖北美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34〕[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一,中國書店1984年影印本,第3頁。〔35〕[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五,第18頁。〔36〕[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第1頁。〔37〕[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第4頁。〔38〕[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一,第26頁。〔39〕[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一,第15頁。〔40〕[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一,第27頁。〔41〕[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第4頁。〔42〕羅竹風《漢語大詞典》卷三,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1頁。〔43〕王云五《叢書集成初編:書譜,續書譜,法書通釋,春雨雜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4頁。〔44〕[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三,第5頁。〔45〕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冊八十六,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50頁。〔46〕羅竹風《漢語大詞典》卷十一,第1311頁。〔47〕[清] 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三,第5頁。〔48〕[日] 白井華陽《畫乘要略·坤》卷三,日本天保二年橋南須原屋茂兵衛刻本,第20頁。〔49〕[清] 王贏《海仙十八描法》,日本文久元年春三月京都洛東錦織邨海仙庵藏識刻本,第1—3頁。〔50〕[清] 王贏《海仙十八描法》,第1—3頁。〔51〕[清] 王贏《海仙十八描法》譜列圖式,第1—9頁。〔52〕漢語大詞典編纂處《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頁。〔53〕徐中舒《漢語大字典》卷六,湖北辭書出版社和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0頁。〔54〕李鶴桐、來一民、陳藝《日語漢字讀音速查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442頁。〔55〕[漢] 楊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1頁。〔56〕[宋]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12頁。〔57〕[明] 張紳《法書通釋》卷下,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第87頁。〔58〕王冬梅《歷代名家書法經典:董其昌〈論書帖〉》,中國書店2014年版,第42頁。〔59〕[漢] 許慎撰,[宋] 徐鉉校《說文解字》卷一,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7頁。〔60〕[清] 馮武《書法正傳》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頁。〔61〕王云五《叢書集成初編:書譜及其他三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頁。〔62〕[宋] 陳思《書苑菁華》卷十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頁。路遙 哈爾濱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講師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