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人生的前線——胡一川藝術(shù)與文獻(xiàn)展”研討會(huì)現(xiàn)場(chǎng)
2020年,為紀(jì)念胡一川誕辰110周年,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與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共同主辦了“站在人生的前線——胡一川藝術(shù)與文獻(xiàn)展”,展覽于11月23日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館開幕,通過呈現(xiàn)胡一川的作品、手稿,以及大量口述史和文獻(xiàn)資料,多角度地回顧了胡一川的藝術(shù)生涯。為進(jìn)一步探討有關(guān)胡一川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學(xué)術(shù)議題,12月22日,“敘事、媒介與跨文化語(yǔ)境:站在人生的前線——胡一川藝術(shù)與文獻(xiàn)展專題研討會(huì)”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館會(huì)議室召開。
本次研討會(huì)邀請(qǐng)了國(guó)內(nèi)十余位學(xué)者進(jìn)行主題發(fā)言,內(nèi)容涵蓋對(duì)本次展覽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以及從圖像與敘事的表達(dá)、媒介與形式的探索、跨文化語(yǔ)境下的實(shí)踐三種不同角度出發(fā)展開的研究。研討會(huì)分上下午兩場(chǎng)進(jìn)行,分別由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胡斌與本次展覽策展人、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史系教授曹慶暉擔(dān)任主持。

與會(huì)嘉賓合影
(一)回顧“胡一川藝術(shù)與文獻(xiàn)展”
本次研討會(huì)為探討“胡一川藝術(shù)與文獻(xiàn)展”在策劃與實(shí)現(xiàn)過程中的問題提供了平臺(tái),此次展覽的策展人、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曹慶暉與展覽設(shè)計(jì)總監(jiān)、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館設(shè)計(jì)部主任紀(jì)玉潔分別對(duì)展覽內(nèi)在與外在的呈現(xiàn)邏輯進(jìn)行了回顧與總結(jié)。

本次展覽策展人、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曹慶暉發(fā)言
曹慶暉從展覽性質(zhì)、內(nèi)容和接受體驗(yàn)等多個(gè)角度,指出了目前展覽存在的問題和改善方向:首先,對(duì)于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美術(shù)與美術(shù)家的回顧性紀(jì)念展,國(guó)內(nèi)仍缺乏常設(shè)性的陳列空間、無(wú)法提供長(zhǎng)線研究的條件,因此在展期較短、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展覽圖錄以及數(shù)字展覽的方式先將展覽“留存下來”;其次,從內(nèi)容上看,本次展覽的呈現(xiàn)邏輯仍相對(duì)單線化,需要進(jìn)一步擴(kuò)大館藏品的征集,形成不同時(shí)空下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對(duì)照關(guān)系,同時(shí)策展人也可以通過虛擬策展的方式對(duì)不同策展思路進(jìn)行比較。此外,本次展覽通過配樂來輔助觀看,為觀眾帶來了綜合性的感覺體驗(yàn),但如何聚焦于展品本身、避免喧賓奪主仍待進(jìn)一步討論;最后,曹慶暉提出,在藝術(shù)家的紀(jì)念性和研究性展覽中,策展人不應(yīng)過分凸顯自身的角色,而需轉(zhuǎn)變?yōu)檎褂[敘事背后的“編劇”,使研究對(duì)象的面貌得到更清晰完整的呈現(xiàn)。

本次展覽的設(shè)計(jì)總監(jiān)、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館設(shè)計(jì)部主任紀(jì)玉潔發(fā)言
紀(jì)玉潔圍繞展覽主色調(diào)與展廳結(jié)構(gòu)分享了本次展覽在視覺傳達(dá)上的設(shè)計(jì)理念。紀(jì)玉潔與設(shè)計(jì)團(tuán)隊(duì)結(jié)合胡一川的身份、性格特征以及藝術(shù)風(fēng)格,將“奮進(jìn)”“強(qiáng)力”“鮮明”定為本次展覽主視覺設(shè)計(jì)的關(guān)鍵詞和基本調(diào)性,從胡一川的作品《牛犋變工隊(duì)》中提取藍(lán)色、從《開鐐》中提取黃色、從《攻城》中提取橙色、從《煤礦》提取灰色等等——最終形成由九種顏色構(gòu)成的色彩系統(tǒng),通過五套不同的色彩組合區(qū)隔出展覽的五大板塊,以色彩帶動(dòng)展覽內(nèi)容的敘事。紀(jì)玉潔認(rèn)為,一場(chǎng)“名家紀(jì)念展”應(yīng)當(dāng)向觀眾呈現(xiàn)一個(gè)立體而豐滿的“人”,以此為出發(fā)點(diǎn),展覽的設(shè)計(jì)語(yǔ)言也應(yīng)當(dāng)具有獨(dú)屬于這名藝術(shù)家的特色。
(二)敘事、媒介與跨文化視角下的
“胡一川藝術(shù)與文獻(xiàn)展”從口述史、美術(shù)作品、美育文獻(xiàn)、人生抉擇等方面切入,對(duì)胡一川的藝術(shù)生涯進(jìn)行了總體性的回顧。而在本次研討會(huì)上,不同學(xué)者圍繞“敘事、媒介與跨文化語(yǔ)境”的主題,從多樣化的視角出發(fā),分享與闡述了針對(duì)胡一川的某件作品或某類創(chuàng)作實(shí)踐所開展的具體研究。
圖像與敘事的表達(dá)
為闡釋作品的意義與藝術(shù)家所傳達(dá)的思想,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藝術(shù)與人文學(xué)院教授李公明、中國(guó)美術(shù)館副研究館員魏祥奇、《美術(shù)》雜志編審&副主編盛葳、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博士鄒佳睿、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創(chuàng)作管理處鄭石如、深圳市關(guān)山月美術(shù)館副研究館員丁瀾翔、西安美術(shù)學(xué)院史論系講師李惠子、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藝術(shù)與人文學(xué)院教授樊林共八位學(xué)者聚焦于胡一川作品的細(xì)部,對(duì)圖像的來源、含義以及圖像產(chǎn)生的歷史原境進(jìn)行了多方位思考與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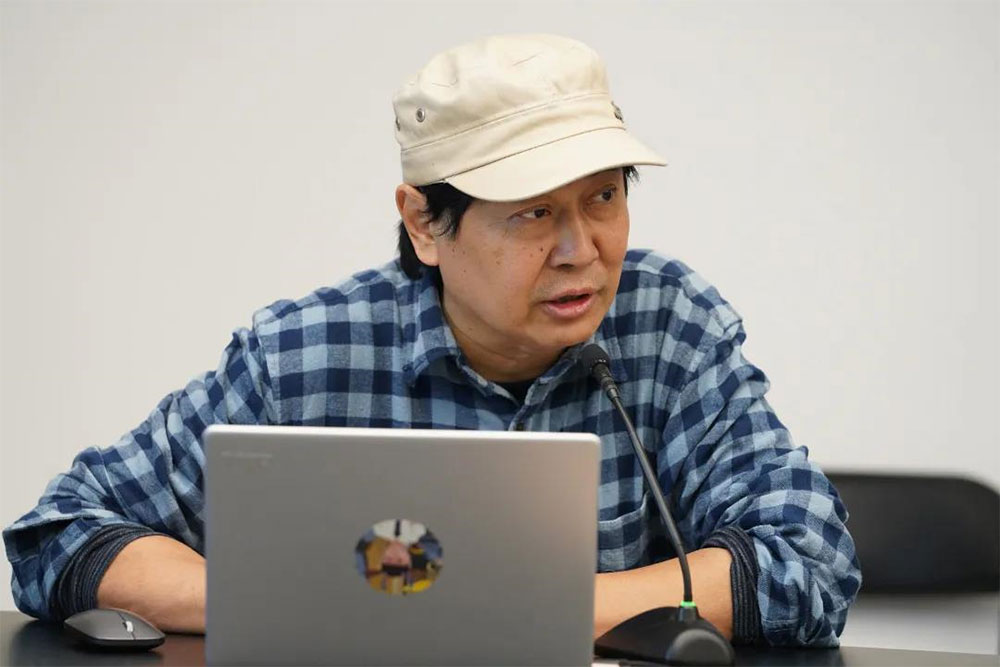
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藝術(shù)與人文學(xué)院教授李公明發(fā)言
李公明從方法論層面探討重返真實(shí)歷史語(yǔ)境、還原圖像原始所指的重要性。他從胡一川的作品《到前線去》《開鐐》出發(fā),結(jié)合廖冰兄、古元等同時(shí)期藝術(shù)家的作品,指出“抗日”或“解放”等主流敘事的固化解讀對(duì)真實(shí)歷史語(yǔ)境與藝術(shù)家原始意圖的遮蔽。這些作品的“經(jīng)典”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來源于主流的宣傳敘事對(duì)真實(shí)語(yǔ)境的有意誤讀。因此,李公明認(rèn)為,當(dāng)下的研究者不應(yīng)把“重返歷史語(yǔ)境”簡(jiǎn)單視為描述圖像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而應(yīng)深入不同層面的歷史狀況,尋找與圖像意圖、形式和傳播效果相匹配的“語(yǔ)境”。

中國(guó)美術(shù)館副研究館員魏祥奇發(fā)言
魏祥奇的發(fā)言主題為“從平民意識(shí)到革命意識(shí)——胡一川早期版畫創(chuàng)作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1930—1937)”。魏祥奇以胡一川早期作品的中“饑民”“流民”演化為后來的“底層勞工”形象切入,他認(rèn)為,隨著左翼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影響的深入,胡一川在1933年之后的創(chuàng)作反映出愈加強(qiáng)烈的階級(jí)斗爭(zhēng)色彩,與先前較為樸素的人道主義形成對(duì)比。前一階段傾向于對(duì)底層人民生存處境的關(guān)懷,后一階段則強(qiáng)調(diào)喚醒與發(fā)動(dòng)民眾奮起反抗,體現(xiàn)了其創(chuàng)作從“平民意識(shí)”向“革命意識(shí)”的轉(zhuǎn)變。

《美術(shù)》雜志編審、副主編盛葳發(fā)言
盛葳通過考察圖像來源與歷史語(yǔ)境對(duì)胡一川《牛犋變工隊(duì)》的主題進(jìn)行闡釋。在盛葳看來,《牛犋變工隊(duì)》不僅呈現(xiàn)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場(chǎng)景,同時(shí)也體現(xiàn)出一種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合作”主題:除了反映當(dāng)時(shí)延安“變工隊(duì)”通過共享勞動(dòng)力和工具來提高效率的生產(chǎn)方式,這種對(duì)“合作”的刻畫或許還暗指政治上的“國(guó)共聯(lián)合”。盛葳認(rèn)為,作為一件懸掛在外交場(chǎng)合的藝術(shù)作品,《牛犋變工隊(duì)》一方面釋放出尋求與美國(guó)合作以解決國(guó)共爭(zhēng)端的積極信號(hào),另一方面又回避了正面沖突,與國(guó)民黨在外交場(chǎng)所懸掛的傳統(tǒng)繪畫拉開差距,于無(wú)形中強(qiáng)調(diào)出藝術(shù)家自身的態(tài)度和立場(chǎng)。

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博士鄒佳睿發(fā)言
鄒佳睿則從解放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歷史背景出發(fā)對(duì)《牛犋變工隊(duì)》展開另一視角的解讀。《牛犋變工隊(duì)》的創(chuàng)作素材來源于胡一川四十年代在下鄉(xiāng)勞動(dòng)過程中的體會(huì),鄒佳睿認(rèn)為,胡一川深入農(nóng)村生活,對(duì)于農(nóng)業(yè)從個(gè)體生產(chǎn)走向集體化的過程有著最直接的體驗(yàn)。相較于同時(shí)期其他藝術(shù)家表現(xiàn)解放區(qū)民俗與風(fēng)情的文學(xué)化處理,《牛犋變工隊(duì)》的圖像并不指向具體的人與事件,而是象征著全體農(nóng)民,胡一川通過概念化和象征化的處理強(qiáng)調(diào)了農(nóng)民形象背后的精神含義,試圖表現(xiàn)由小農(nóng)向集體的轉(zhuǎn)變以及由生產(chǎn)向大生產(chǎn)的轉(zhuǎn)變。

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創(chuàng)作管理處鄭石如發(fā)言

深圳市關(guān)山月美術(shù)館副研究館員丁瀾翔視頻發(fā)言

西安美術(shù)學(xué)院史論系講師、新中國(guó)美術(shù)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惠子發(fā)言

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藝術(shù)與人文學(xué)院教授樊林發(fā)言
鄭石如與丁瀾翔分別從圖史關(guān)系與圖像來源出發(fā)解讀了1948年胡一川的第一幅主題性油畫作品《攻城》;李惠子結(jié)合胡一川日記等文獻(xiàn),梳理了胡一川1942年作品《轟炸敵艦》的創(chuàng)作歷程,以及“轟炸”圖示在傳播過程中的內(nèi)涵與意圖。三位學(xué)者都通過個(gè)案研究表明,胡一川的主題性創(chuàng)作并不僅僅是為了配合政治宣傳任務(wù),還折射出藝術(shù)家對(duì)時(shí)事的自覺思考以及借助“主題”來探索民族性藝術(shù)形式的創(chuàng)作策略;樊林則進(jìn)行了“關(guān)系史”的整理,從胡一川在廣州美院的同仁、美術(shù)史論家遲軻的視角出發(fā),為還原胡一川所處的思考、創(chuàng)作語(yǔ)境提供了線索。
媒介與形式的探索
五十年代以前,胡一川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以木刻版畫為主要媒介,從三十年代初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的黑白木刻到抗戰(zhàn)以來的套色木刻,胡一川的創(chuàng)作理念經(jīng)歷了怎樣轉(zhuǎn)變?他對(duì)于形式語(yǔ)言的探索作出了哪些努力?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國(guó)家主題性美術(shù)創(chuàng)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小鳳、中山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助理教授艾姝、《美術(shù)》雜志責(zé)任編輯楊燦偉、重慶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講師郝斌、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冷俊岐共五位學(xué)者通過不同的案例研究為上述問題提供了思路與線索。

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國(guó)家主題性美術(shù)創(chuàng)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小鳳發(fā)言
曾小鳳從胡一川的《征輪》出發(fā)探討了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與一八藝社、左翼作家聯(lián)盟之間的關(guān)系。魯迅1931年在左聯(lián)機(jī)關(guān)報(bào)《文藝新聞》上發(fā)表《一八藝社習(xí)作展覽會(huì)小引》一文,以胡一川的《征輪》作為配圖,提出了版畫對(duì)革命宣傳的重大意義。《征輪》成為魯迅《小引》的配圖,在曾小鳳看來具有多重意味,一方面作品中的“輪子”是當(dāng)時(shí)左翼文藝界常見的視覺符號(hào),象征著革命與出征,另一方面,胡一川當(dāng)時(shí)所在的一八藝社正是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發(fā)端時(shí)的一支重要力量,《征輪》在木刻運(yùn)動(dòng)發(fā)起者魯迅眼中或許具有一定的標(biāo)志性意義。

中山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助理教授艾姝發(fā)言
艾姝針對(duì)胡一川“標(biāo)語(yǔ)畫”作品的形式展開分析。“標(biāo)語(yǔ)畫”指三十年代以來,以“群眾”“怒吼”“喊口號(hào)”作為典型的圖像模式的主流革命宣傳版畫。艾姝認(rèn)為,雖然政治宣傳畫的圖像通常較為模式化,但胡一川對(duì)形式語(yǔ)言仍進(jìn)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他既參照了前人的圖示,同時(shí)又在構(gòu)圖、景別、細(xì)節(jié)處理上有所創(chuàng)新,這些新變化一方面可能與黑白木刻向套色木刻的媒介轉(zhuǎn)變與印刷能力的提升有關(guān),另一方面則在于他反對(duì)“千篇一律”的觀念,胡一川三十年代的日記中記錄了以多種形式和內(nèi)容開展的宣傳活動(dòng),反映出他對(duì)待宣傳工作時(shí)“靈活應(yīng)變”的態(tài)度。

?《美術(shù)》雜志責(zé)任編輯楊燦偉發(fā)言
楊燦偉圍繞“胡一川在魯藝木刻工作團(tuán)的表現(xiàn)轉(zhuǎn)向及其背后策略”,提出在魯藝木刻工作團(tuán)時(shí)期胡一川創(chuàng)作活動(dòng)背后的三組矛盾:對(duì)胡一川而言,這一時(shí)期的藝術(shù)實(shí)踐是“工作”還是“創(chuàng)作”?面向的是群眾還是自己?從黑白到套色的轉(zhuǎn)變是出于強(qiáng)化宣傳效果還是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基于對(duì)這一時(shí)期作品的分析,楊燦偉認(rèn)為胡一川采用了一種折中風(fēng)格,他既配合政治宣傳,將木刻視為工作,迎合群眾的審美——尤其體現(xiàn)在其口號(hào)化、標(biāo)語(yǔ)化特征明顯的畫風(fēng)上;同時(shí)他又排斥固化的形式主義,力圖進(jìn)一步探索畫面表現(xiàn)力——這也是他當(dāng)時(shí)被評(píng)價(jià)為風(fēng)格不夠“大眾化”、“主題”不夠清晰的原因之一。

重慶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講師郝斌發(fā)言
郝斌在“探索民族形式”的語(yǔ)境下考察了胡一川三四十年代版畫在線條與色彩上的轉(zhuǎn)型。郝斌將胡一川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分為“黑色胡一川”和“色彩胡一川”時(shí)期。在前一個(gè)階段,胡一川提出要將線條的表現(xiàn)力作為樹立黑白木刻民族風(fēng)格的關(guān)鍵。四十年代后,隨著對(duì)年畫、水印木刻等民間美術(shù)的發(fā)掘,胡一川逐漸傾向套色木刻的創(chuàng)作,這一時(shí)期他試圖探索的“色彩”不只是顏料層面的色彩,還意味著風(fēng)格層面的“地方色彩”。郝斌認(rèn)為,胡一川四十年代下鄉(xiāng)走入大眾的生活經(jīng)歷推動(dòng)了其創(chuàng)作的“色彩”轉(zhuǎn)向。
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冷俊岐發(fā)言
冷俊岐圍繞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敵偽宣傳畫與胡一川在魯藝木刻團(tuán)創(chuàng)作的“新年畫”展開了對(duì)比研究。自1938年抗日戰(zhàn)爭(zhēng)進(jìn)入相持階段后,日軍的“宣撫班”開始繪制大量欺騙性的宣傳畫,企圖籠絡(luò)淪陷區(qū)的中國(guó)平民。胡一川所在的魯藝木刻團(tuán)為對(duì)抗日軍的宣傳戰(zhàn)術(shù),受傳統(tǒng)民間年畫的啟發(fā)創(chuàng)作了一批“新年畫”:在形式上,不同于敵偽宣傳畫對(duì)封建迷信元素的套用,“新年畫”剔除了糟粕,保留了具有吉祥意味的構(gòu)圖形式與裝飾紋樣;而在內(nèi)容上,民眾被塑造為反抗者,不再是敵偽宣傳畫中處于邊緣的“順民”。冷俊岐認(rèn)為,“新年畫”的出現(xiàn)不僅是對(duì)民族性版畫形式的探索,同時(shí)也意味著廣大民眾不再只是宣傳的對(duì)象,而是抗日過程中需要聯(lián)合與發(fā)動(dòng)的革命主體。
跨文化語(yǔ)境下的實(shí)踐
胡一川的油畫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以來被蘇派油畫的推崇者評(píng)價(jià)為“土油畫”,此處的“土”與其本土化的實(shí)驗(yàn)是否有關(guān)?又與西歐的現(xiàn)代派油畫之間存在怎樣的聯(lián)系?沿此思路,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藝術(shù)與人文學(xué)院副教授蔡濤、藝術(shù)家&策展人劉鼎、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巴音娜共三位學(xué)者從跨文化語(yǔ)境的研究視角出發(fā)展開探討。

?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藝術(shù)與人文學(xué)院副教授蔡濤發(fā)言
蔡濤回顧了三十年代胡一川在杭州國(guó)立藝專學(xué)習(xí)期間的兩位“外教”——來自法國(guó)的克羅多與日本的齋藤佳三,兩者都曾提出“藝術(shù)無(wú)國(guó)界”的觀點(diǎn),并熱衷于跨媒介的藝術(shù)實(shí)踐,同時(shí)對(duì)左翼運(yùn)動(dòng)抱有關(guān)切與同情,胡一川在兩位外籍教師熏陶之下形成的“國(guó)際視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后來貫通版畫、油畫乃至戲劇、音樂、書法等媒介的創(chuàng)作方式,然而,胡一川在五六十年代的日記中卻極少提及對(duì)現(xiàn)代主義的理解。胡一川1957年在一則日記中所提及了“席箱”一詞,據(jù)蔡濤的考證,“席箱”指的是塞尚,這是塞尚在胡一川日記中唯一的一次記錄,他似乎有意克制關(guān)于現(xiàn)代主義的論述,蔡濤認(rèn)為這可能是出于在特定的歷史時(shí)期的自我保護(hù)策略。

藝術(shù)家、策展人劉鼎發(fā)言
劉鼎聚焦于七八十年代胡一川的油畫作品,對(duì)其開放與融合的創(chuàng)作理念展開討論。在1977年廣州美院的開學(xué)典禮上,胡一川重提“百花齊放”,劉鼎認(rèn)為這不只是對(duì)1957年“雙百方針”援引,更有可能指向的是一種新的轉(zhuǎn)變——面向整個(gè)世界而不再只是“共產(chǎn)主義世界”的“百花齊放”。在這一背景下,胡一川在創(chuàng)作中“重啟”了過去掌握的資源,其概括性筆觸既彰顯出對(duì)現(xiàn)代派風(fēng)格的熱愛,暗部的斑斕又反映出從蘇聯(lián)油畫中習(xí)得的用色能力。

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巴音娜發(fā)言
巴音娜對(duì)胡一川油畫創(chuàng)作在不同時(shí)期的呈現(xiàn)面貌進(jìn)行了梳理:在杭州藝專學(xué)習(xí)期間,胡一川更傾向于來自西方現(xiàn)代派的形式主義。隨著延安整風(fēng)運(yùn)動(dòng)的開展到五十年代初蘇聯(lián)油畫訓(xùn)練班的引入,胡一川對(duì)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新思考使其強(qiáng)烈的表現(xiàn)性風(fēng)格轉(zhuǎn)換為符合左翼語(yǔ)境的形式,筆觸趨于細(xì)膩、色調(diào)趨于灰暗。1960年訪蘇期間胡一川接觸到了塞尚的作品,回國(guó)后又恰逢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塞尚熱”的興起,他對(duì)現(xiàn)代主義的重新發(fā)掘與突破蘇聯(lián)模式窠臼的訴求,促使其油畫又回歸到表現(xiàn)性的風(fēng)格上。巴音娜認(rèn)為,胡一川的油畫風(fēng)格從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中來,又結(jié)合長(zhǎng)期以來民族性版畫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yàn),回到一種由自身生發(fā)的“中國(guó)化的現(xiàn)代”中去。

本次研討會(huì)主持人、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胡斌發(fā)言
“胡一川藝術(shù)與文獻(xiàn)展”通過文獻(xiàn)的介入使得觀眾在藝術(shù)作品之外,能從更多元的視角與維度了解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生涯。從展覽延伸至本次研討會(huì),不同學(xué)者在面對(duì)同一件作品、同一類題材時(shí)也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和解讀方法,正如主持人胡斌在會(huì)議總結(jié)中所言:“多元視角的共生與對(duì)話是研究走向深入的標(biāo)志之一”,他表示,關(guān)于胡一川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討論仍有擴(kuò)展空間,此外,從研討會(huì)的主題報(bào)告到形成深度的學(xué)術(shù)文章還有更長(zhǎng)的路要走,展覽、研討會(huì)的舉辦,能夠吸引更多學(xué)者對(duì)胡一川乃至對(duì)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的關(guān)注。


“站在人生的前線——胡一川藝術(shù)與文獻(xiàn)展”研討會(huì)現(xiàn)場(chǎng)







 皖公網(wǎng)安備 34010402700602號(hào)
皖公網(wǎng)安備 34010402700602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