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文心,《內存腐蝕》截屏,2017.
“不可退出”是當下社會狀態中隱而不現之物,同時也是流媒體平臺的扭結所在。
“讓我在自己家里變成一扇門,我可以永遠出門永遠進門。”——金武林《變形記》
幾個月前,我的手機收到好朋友楊紫發來的一張在線影院觀影票。由他策劃的這個題為“夢飲酒者”的線上觀影單元共由11部影像作品組成,作者均為當代藝術家,片長從幾分鐘到幾十分鐘不等。掃碼進入“影院”,卻發現上映內容很難一次性看完,實際上在第三件作品出場之后,我就遭遇了強烈暈眩感的襲擊,并直接招致了一段計劃外睡眠。該反應與主題如此契合,如同策展的一部分。以隨手分享影票圖片的方式,二維碼如同墻上的門,規定了觀眾的進入方式。在健康碼尚未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之前,少有人意識到我們通過它只能進入,而無法退出。正如在此之前,我也從未意識到在真實的展廳中,那扇可以隨時退出的大門在觀展體驗中竟占據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在“夢飲酒者”中,除非粗暴地退出程序,否則進度條就是一條你被卷入其中的翻涌的河流,在勢能耗盡,百川入海之前無法被釋出。
“不可退出”是當下社會狀態中隱而不現之物,同時也是流媒體平臺的扭結所在。尚未微型化的臺式甚至柜式計算機曾試圖偽裝成普通家具,使自己駐留在“打開新世界的大門”這一富有希望的修辭之中。隨著計算機微型化和存儲量激增,社交網絡大行其道的背后則是不加選擇的本地存儲。不再是門的微型化手持媒體成為了一個個昏暗的地窖,通過瘋狂存儲,我們也被二維碼不斷地吸入到其他存儲空間中。在公共場所每天都會被跌落的手機吸引片刻注意力的我們,卻神奇地未曾意識到自己所處的這種“不可退出性”的單向度進程。
“不可退出”或“無法退場”,如果沒有觸及到這一真相,任何一種所謂“線上策展”都會因為低效的觀看體驗而趨于平庸,因其仍將微型或手持媒介視為現實空間的通道。如同大銀幕與流媒體之間的致命差別一樣:一種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持續對抗在現實空間中以象征性的形態發生,而流媒體則重新喚回了被影像最大限度拆除的“第四面墻”,變成了一種自我專制與他人專制之間的無緩沖對抗。相比于被導演與剪輯師處理過的影像,對于在特殊社會狀態下失去現實空間的藝術來說,“第四面墻”的復魅傷害是更為致命的。在鮑里斯·格羅伊斯(Boris Groys)看來,策展人曾以公意之名管理象征性空間,觀眾作為該空間(它必須與可退至的外部空間保持連通)的所有者對抗著藝術自律的專制。正是在藝術的“法的門前”,策展人用“專門為觀者所設的門”的方式稀釋著“第四面墻”。他的任務在于保持真實界與想象界不會直接撞擊:前者是藝術家施于作品的數據編碼,后者是觀眾所渴望的自控與認同。“不可退出”是象征界的消失,少有人有意識地體驗過象征界消失的世界(雖然很多人曾經在婁燁的手持鏡頭中體驗過這種生存狀態)。

周巖,《我們倆:游戲漫游》截屏,2018-2019.
人們通常傾向于把“夢”與“醉”理解為一種或迷狂或優美的審美范疇,卻忽略了“不可退出”才更精確地描述了這類體驗,除了等待這一空間自行將你排出體外絕無中止的可能。將空間性的藝術裝置復歸于媒介中的數據流態,藝術作品自身的媒介性就被取消了,正如暈眩感(娜塔莉·杜爾伯格&漢斯·博格在《How to Slay a Demon》中通過切割第一人稱視角所帶來的)和對專注度的直接捕獲(周巖,《我們倆:游戲漫游》中的畫外音和引導觀者打開開關的設定),它們因為象征界的消失而凌駕于作品的“意義”之上。而觀者則直接被吸入數據流內部,主體性如在留聲機的轉盤上被甩干。
事實上,真實界對于想象界的直接銘寫早在1900年左右就曾以“影響機器”(influencing machine)的形態出現過。當時最著名的偏執癥患者法官丹尼爾·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人類靈魂藏于身體神經之中”的觀念如何迫使他不斷幻想各種電信通訊模型以形成自己的宇宙論。在德國媒介學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解讀中,這種妄想表達了一種避開感性干擾,直接記錄真實界的可能,等待某種類人書寫機器將其無損解讀。這一極其類似于弗洛伊德“力比多灌注”(libidinal cathexis)的妄想曾令后者感到不安,它暴露了“心理分析”所掩蓋的夢的原始機制。在“影響機器”幻想中,還存在著一種對于上帝在這一信息網絡中威脅自身存在的擔憂:上帝本人無法區分潛藏于人心底的死寂的自我(在弗洛伊德處被偽裝成童年經驗的東西)和此刻活著的人,從而無法得到被甄選的高效信息回饋,被纏繞于過分冗雜的神經之中。在那一代人樸素的臆想中,他們形容上帝會“撥錯電話”(在阿米爾汗的電影《P.K.》中,他使用了這一隱喻來說明宗教沖突)。“夢”的媒介機制實際上困住了信息的發出者與接收者兩級,藝術家所編織的信息閉合之網,同時也為自己所做。
某種意義上說,新媒體藝術趨向于信息銘寫(被視為心靈感應)妄想的最終達成,凸顯這一舊時妄想的當下結界化便是此類藝術與策展要給出的東西。于是,如果說在過去的“批判藝術”時代,藝術的任務在于揭露某種虛假意識,告訴人們“真實實為妄想”,那么新媒體藝術則需要告訴人們“妄想已然為真”。但從齊澤克“享受你的癥狀”那里回退一步,“不可退出”所帶來的“無法享受”仍是我們能意識到的問題。新媒體藝術家們在偌大的工作室中使用著家具一般的工作站,自認仍站在新世界的門前,在建模和渲染的工序中穿梭于作為象征界的私人記憶——如張文心在《內存腐蝕》中所呈現的藝術家作為自己記憶之策展人的意圖,卻可能未曾想到其中所生成的媒介壓迫(比如對于手持終端的使用者),以及藝術家的自我剝削。我們必須對這種數字經濟中的數量級壓迫有所意識:一種新的數字藝術體制中的階級意識,同時也是這個時代階級意識的新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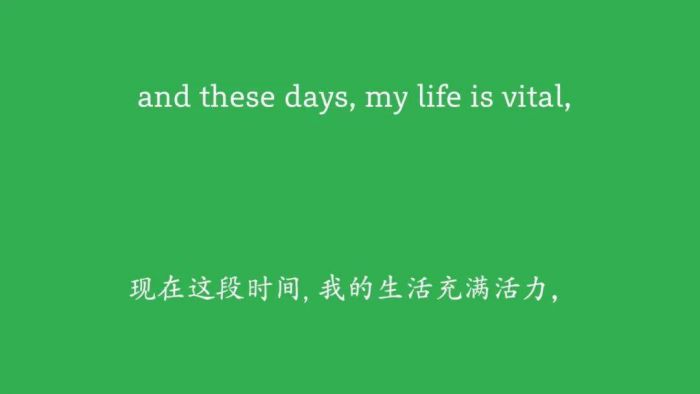
趙要,《有神的信號 - 抑郁癥,我們分享的秘密》截屏,2018.
“夢飲酒者”似乎在尋找傳達這一危機的方式,策展人也似乎有意地對這一封閉的媒介空間中的生存姿態進行了融合:旋轉對于注意力的捕捉(陳天灼,《拉西亞》)、私人空間中的亞空間躍遷(《我們倆:游戲漫游》)、第一人稱視角的切割(《How to Slay a Demon》)、勻速行進的數碼有機體(《內存腐蝕》)……假如普遍性(哲學與科學)與個體性(藝術與經驗)不再被肉身的我們所中介,這樣的世界是可以承受的么?在“夢飲酒者”的終章(趙要,《有神的信號》),被之前所有作品消耗得精疲力竭的我,舒適地讀完(聽完以及看完)了所有字句。這樣的字句或者說信號,也會遵循“黑暗森林”法則,被某種對抑郁癥懷有敵意的存在所抹殺么?不,也許更為糟糕,由于“不可退出”的社會機制不再有一個可被想象的外部,即使是一種值得時刻警戒的鮮活的外部威脅都是不可得的,當下時代的威脅更多地來自于內部,也湮滅于內部。這也是新媒介潛藏的暴力所在:被時刻上傳,而又時刻無法上傳或表達。
當藝術力圖拆除“第四堵墻”,以便讓觀眾不再是旁觀者時,這面墻到底是被摧毀了還是被重置了?在被作為拆遷補償的反思判斷力失去了現實連接之后,我們又何嘗不處于“成為墻”這件事本身的誘惑之中?也許在經典美學家那里被承諾為反思判斷力的東西,在新媒體藝術家及其策展中應被轉為一種窮竭一切的行動力。就像《內存腐蝕》中行走的軀體,卻需要一種更快的勻速……
比如想象自己是一道光,只遵循最基本的光學原理,被不斷的折射與反射,直到探明所有的墻。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