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守謙作為一位在中國和北美接受過嚴格的藝術史訓練、在大學與博物館來回穿梭的學者,他的每一篇論文及由論文匯編而成的每一本著作,都給人以深刻的啟發。本文將分兩部分來討論他的新書《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簡體中文版2019年出版)。第一部分介紹書中的主要觀點,第二部分嘗試把這本書放在石守謙的學術脈絡及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整體脈絡中來略做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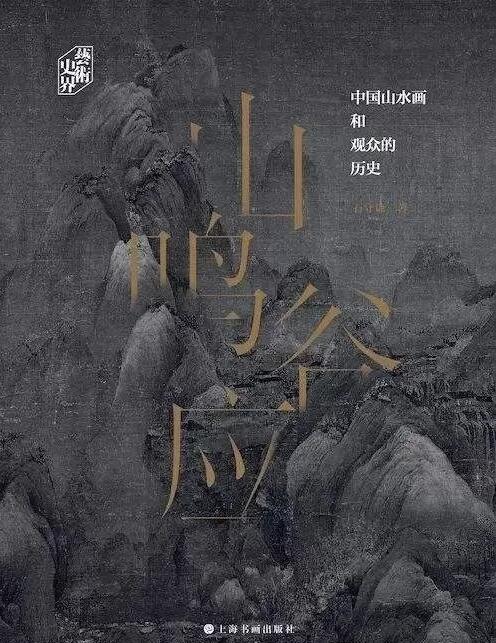
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
石守謙 / 著
京不特 / 譯
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11
《山鳴谷應》是一部由問題串聯起來的中國山水畫通史。這么一說,腦中浮現出的是在大學時代對筆者影響很大的陳傳席的《中國山水畫史》(1988年初版)。簡單來說,想一句話歸納陳著是不可能的,勉強可概括為:它全面梳理了山水畫(家)的基本文獻與圖像。但石著卻可很容易地歸納為:作者追問了“中國山水畫為什么能夠形成‘歷史’(風格史和觀念史)”這個問題,并從畫家與觀者互動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答。因為有這個核心問題的支撐,盡管全書體量不小(簡體中文版近500頁),卻能讓人一氣讀完。
此書的問題意識鮮明地體現在副標題“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中。主標題“山鳴谷應”也很妙,用山川中人的回聲凸顯山水畫與觀者互動的主題。在總主題之下,全書12章的分主題也十分鮮明。每一章都交織著隱顯兩條線索:“顯”的是不同時代的山水畫變遷,“隱”的則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社會身份的觀者的思想變化。
第一章“序論 :山水畫前史”說明了全書為什么要從“畫家與觀眾互動”的角度講述山水畫的歷史。作者的思考過程是這樣的:山水畫為什么在中國繪畫中具有崇高地位?因為山水畫具有特殊的意義。山水畫的意義不斷發生變遷,形成了山水畫的歷史。為什么山水畫的意義會不斷變遷?是因為始終有觀眾的參與。山水畫的意義(作者用“意涵”一詞)主要是觀念層面的,但也包括風格層面的。為了更好地統一觀念與風格這兩個層面,作者提出“畫意”的概念。并以有無“畫意”為標準,判定山水畫的歷史應該從10世紀開始。
第二章“山水畫意與士大夫觀眾”講述的是山水畫歷史的第一個階段,大致在10世紀中期到11世紀中期之間。作者討論了幾個問題,分別對應這一章中的三個小節:為什么從五代開始,山水畫突然得到迅速發展,并出現了隱士主題?為什么北宋初年的山水畫中出現了大量對行旅人物活動的描繪?為什么士大夫文官大量歌詠山水畫?這一章認為,五代到北宋中期的約100年間,士大夫文官階層是山水畫的欣賞主體,山水畫也因此形成了以隱居、官員遷徙的行旅、表現公務生涯中的精神寄托為主題的畫意。
第三章“帝國和江湖意象:1100年前后山水畫的雙峰”討論的是北宋后期山水畫發生的一次重要轉變,即政治性的山水(作者稱之為“帝國山水”)與反映私人情感的文人山水(作者稱之為“江湖山水”)的興起。這兩種蘊含不同畫意的山水畫分別代表了以帝王為中心的具有政治身份的觀者和有意消除政治身份的以文官群體為主的觀者。和上一章的士大夫文官觀者有所不同,這一階段的文官士大夫生活在北宋后期巨大的政治壓力中,他們是失意文官,是努力解除政治牽掛的已經離職或做好離職準備的文官。在這種政治語境中,“帝國山水”的代表是宮廷畫家的繪畫、帝王的繪畫,如郭熙的《早春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宋徽宗的《雪江歸棹圖》等。“江湖山水”的代表是郭熙為離職文官所畫的《樹色平遠圖》等以朦朧煙云為重要特征、體現瀟湘主題的繪畫,尤其是“米氏云山”和蘇軾交游圈中的繪畫,如王詵的《煙江疊嶂圖》。作者也因此討論了典型的失意文官蘇軾和以他的經歷與詩文為主題的繪畫,如喬仲常的《后赤壁賦圖》。

《早春圖》郭熙(北宋),絹本,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樹色平遠圖》郭熙(北宋),絹本,現藏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第四章“宮苑山水與南渡皇室觀眾”討論的是為什么南宋的宮廷山水畫會得到如此繁榮的發展,并形成淡化政治色彩的詩意化特征。在第三章,作者要努力闡述與“江湖山水”對應的失意文官觀眾與北宋初年的士大夫文官觀眾的區別;在第四章,作者也要極力說明南宋和北宋后期的宮廷和皇家觀眾有什么不同。作者不同意以往簡單地認為南宋宮廷山水畫形成詩意化特征是因為受到文人文化的影響的觀點,批評其為“文人中心主義”。他認為應該放在南宋的政治大環境中去看,即南宋宮廷抱有一種“過渡”的心態,因此對山水畫的要求從表現北宋帝國山水的雄心,轉向體現宮廷燕游之安樂閑適。
第五章“趙孟頫乙未自燕回的前后:元初文人山水畫與金代士人文化”討論的是美術史中的一個大命題——元代變革。在山水畫中,這種變革集中體現在兩點:一是“復古”,二是書法入畫。為此,盡管和大多數學者一樣,作者也聚焦于趙孟頫,但卻獨出新意,沒有討論他的個人畫藝,而是以他為線索,討論元代初年文人山水畫的形成與特殊的文人文化圈的關系。作者認為,趙孟頫和他身邊的江南文人圈之所以發生轉變,與他們接觸到的金代文人文化有直接關系。在這個思路下,作者先是重新討論了金代山水繪畫和圖像,如武元直的《赤壁圖》和李山的《風雪杉松圖》中的懷古主題、金代磁州窯生產的磁枕上的山水圖像和墓葬中山水壁畫反映的民間宗教趣味;然后討論元代初年北方地區直接傳承自金代傳統的山水畫;最后再落腳到趙孟頫,討論了他在北方為官后回到江南,其繪畫開始強調古意,書法用筆出現新的畫意。

《赤壁圖》武元直(金),紙本,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磁州窯白釉黑褐彩蘆葦仙鶴紋枕(金),來源:河北博物院官網
第六章“趙孟頫的繼承者:元末隱居山水圖及觀眾的分化”討論的是以“元四家”為代表的元末山水畫,其主要特征可概括為“書齋山水”(何惠鑒語)及“地產式山水”(Landscapeof Property,文以誠語)。作者基于畫意的概念,將之定義為“隱居山水圖”。在這一章,作者要回答的是元末的文人隱居山水與宋代的不同。同樣,突破口也在于觀眾的不同。作者對“元四家”一一進行了討論:先是討論吳鎮繪畫中典型的“漁隱圖”模式及這種畫意與隱居不仕的文人觀者的關系;然后討論倪瓚及其繪畫中看似平淡的水邊空亭的隱居生活所折射出的戲劇性的個人生活變遷;接著討論黃公望繪畫中的道教因素。這三個人的繪畫都有關隱居,但卻是不同原因的隱居。在這一章最后兩節,作者把隱居圖的觀者放大到了群體,先從馬琬和張渥為楊竹西所作的隱居圖來討論元末隱居山水中的富裕士紳觀眾,最后借“元四家”的第四人王蒙頗具動感的隱居圖討論元末蘇州地區雖處于隱居狀態但卻躍躍欲試想在劇烈的社會政治變動中建功立業的文人群體。正是這些在不同的隱居圖里表現出不同狀態與心態的觀眾,賦予了元末山水畫特殊的面貌。
第七章“明朝宮廷中的山水畫”重新處理了明代宮廷繪畫與“浙派”的問題。宮廷繪畫當然是為宮廷觀者所作,但作者的新意在于,他認為從明代初年到后期宮廷山水畫脈絡的變化,基本都與帝王觀眾的轉變有關。比如,明初宮廷與西藏僧侶的密切關系,使受到佛教繪畫影響的青綠山水成為宮廷山水畫的主流。皇帝變了,趣味隨之轉變——正如簡樸的宣德皇帝喜歡簡樸的水墨山水,追求個性的成化皇帝喜歡吳偉狂肆的畫風。除皇帝外,宮廷觀眾還包括明代的宦官和藩王,作者也討論了他們對山水畫的影響。這一章最后還討論了“浙派”晚期繪畫與道教社團的觀眾之間的關系。
第八章“明代江南文人社群與山水畫”其實是第七章的姊妹篇,討論的是明代以蘇州為中心的文人畫藝術的出現和發展。在作者看來,正是由于明代發達的宮廷藝術,才會出現相對應的文人藝術。如果說宮廷山水畫是“專業”的,文人山水畫強調的就是“非專業性”,并刻意與宮廷繪畫劃清界限。作者認為,到了明代,文人山水畫變成了一種普遍現象,所以要從更普遍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文人社群的角度來討論其畫意和觀眾之間的關系。這一章處理的問題很多。作者先是在明代的文人山水畫中區分出“雅集山水圖”“紀游圖”“茶事圖”“別號圖”等不同畫意的類型,來進行社會史式的討論;同時也處理了從“吳門畫派”過渡到以董其昌為代表的“松江畫派”的傳統主題。作者意識到,明代的文人文化中也包括一些試圖進入精英文化圈的文化新貴,他們與職業畫師的繪畫有著密切的互動。此外,作者還關注女性觀者,討論了仇英的“閨情山水”。這一章最后還討論了晚明文人中大量出現的佛教“居士”與山水畫中具有宗教意義的畫意之間的關系。
第九章“17 世紀的奇觀山水:從《海內奇觀》到石濤的奇觀造境”討論的是明末清初山水畫中的尚“奇”風尚,以及由此形成的“奇觀山水”。與明代中期以來紀游圖式“實景山水”不同,“奇觀山水”刻意凸顯奇特視覺經驗,與旅游文化和大眾文化有密切關系。在這個背景下,清初以石濤為代表的一批畫家有意識地要超越流行的大眾圖像,創造出了新的“奇觀山水”。石濤的新繪畫對應了新觀眾,其中,作者著重分析了旗籍地方官員和徽州商人這兩類。作者還把眼光放寬到東亞的范疇,討論了“奇觀山水”通過使節傳播到朝鮮的情況。通過跨文化的比較,作者注意到了“奇觀山水”背后隱藏的國際文化競爭。
第十章“以筆墨合天地:對18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和第十一章“變觀眾為作者:18 世紀以后宮廷外的山水畫”也堪稱姊妹篇。前者討論了清代中期宮廷山水畫和宮廷觀眾的互動關系,后者討論了清代中期和后期社會中山水畫的新趨勢和觀眾群體的新變化。清代宮廷山水畫和宮廷觀眾與宋代、明代有什么不同呢?簡言之,清代宮廷在部分接受西洋藝術風格的基礎上,重拾對明代以來實景山水的特殊興趣。因此,宮廷畫家和與清代文化有關聯的旗籍畫家創造性地發展出一種將以“四王”為代表的正統派畫風與新的自然觀察方法相結合的“巨觀山水”。而在宮廷文化之外,以《芥子園畫譜》為代表的版畫畫譜使山水畫成為簡便易學的技藝。于是,畫家與觀眾的關系出現了新變化——觀眾同時也是畫家。這便帶來了一系列的影響:專業畫家為了與通過畫譜自學的人相區別,會刻意描繪畫譜以外的題材,比如庭院山水,其作品也因此流行起來,袁江、袁耀的園林界畫就是其中的代表。以黃易為代表的低級幕僚所作的山水畫和“訪碑圖”則是另一種成果。此外,19世紀一些心懷經世致用抱負的文人自己也能作畫,就可以相對自由地發展出一種對地理新景觀的探索。
第十二章“迎向現代觀眾:名山奇勝與20世紀前期中國山水畫的轉化”作為這本書的終章,討論了20世紀前期新的觀眾群體的形成與山水畫在功能、形式與畫意上的巨大轉變。出于對真實感的追求,畫家會借助攝影照片進行繪畫,同時把傳統的寫生、臨摹加以新變。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一種“名山奇勝”山水。在作者看來,這是中國山水畫史中最具有觀眾意識的時代,也是藝術邁向“現代”的標志。
《山鳴谷應》與作者的前幾部著作相比,有明顯的傳承與發展關系,給人以“集大成”之感。石守謙在其最早的論文集《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1996年)中提出中國繪畫研究的基本理念,即關注文化史范疇內的風格史變遷。從這本文集的幾篇論文中,尤其是討論“浙派”繪畫的興衰與貴族品位的關系及討論“吳門繪畫”中的“避居山水”與蘇州失意文人之間關系的論文,已經可以明顯看到作者對觀眾的討論。文集中的第一篇《文化史范疇中的畫史之變》,簡直就是《山鳴谷應》的萌芽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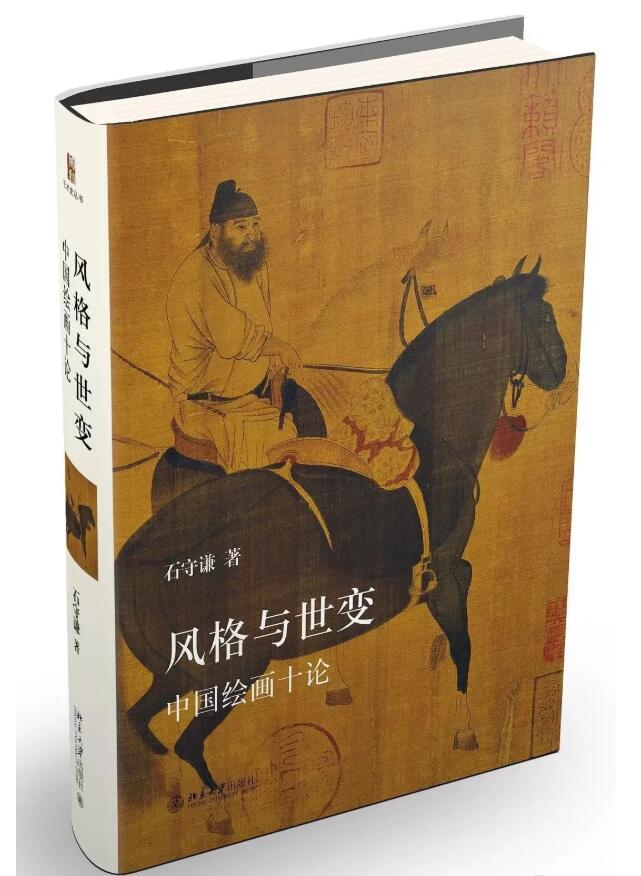
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
石守謙 /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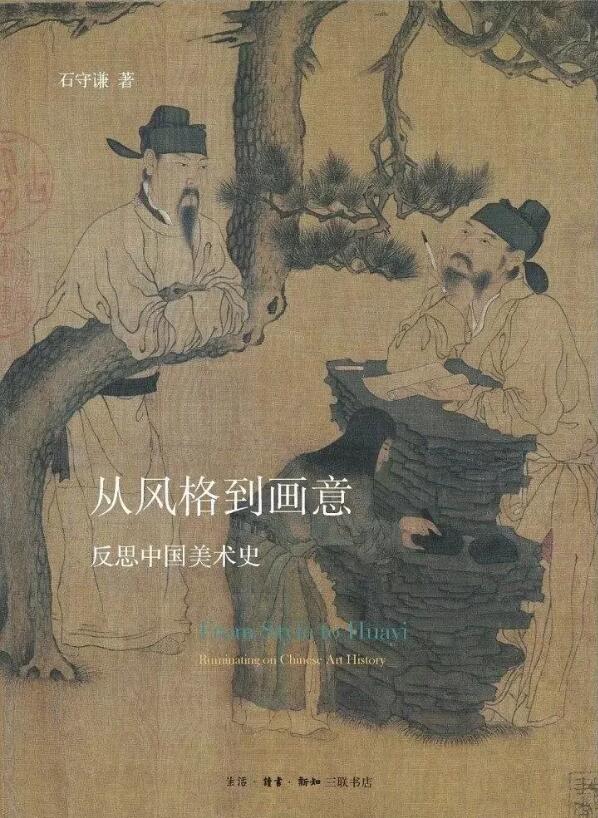
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
石守謙 /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08
在之后的第二本文集《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2010年)中,石守謙完成了其研究理念的升華,即把對繪畫史的討論重點從風格史轉向了“畫意”。其中最主要的論文是《風格、畫意與畫史重建——以傳董源〈溪岸圖〉為例的思考》,第一次完整提出了“畫意”的研究思路。這篇發表于2001年的論文,寫作背景是1999年末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行的圍繞《溪岸圖》真偽的大討論。這次眾所周知的、充滿戲劇性的討論帶來的影響,至今尚未完全消散——無論是對于直接辯論的雙方(高居翰和方聞),還是對參與討論的其他學者。方聞認為《溪岸圖》很可能是董源之作,高居翰(James Cahill)則認為是張大千偽作。問題就在于對山水畫,特別是對早期山水畫的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分歧,看似科學的形式分析在不同人的理解和使用中有很大的不同。與《溪岸圖》真偽討論伴生的,是方聞和高居翰的另一次隔空討論。高居翰在發表對《溪岸圖》質疑的同時,還發表了《關于中國畫“歷史”與“后歷史”的一些思考》一文(Some Thoughts on the History and Post-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1999年11月講座文稿,2005年正式出版),提出了“中國繪畫史的終結”的說法,在某種意義上對風格史的有效性提出了懷疑。而方聞很快撰寫了《為什么中國繪畫是歷史?》(2003年)一文作為間接的回應,試圖闡述為什么中國繪畫具有獨特的、不同于西方的風格史。
以己意猜想,我認為作為方聞高足的石守謙在深刻思索并試圖調和老師與高居翰的爭論中,反映出了為中國繪畫建立一部“歷史”的困境。方聞與高居翰之所以是海外中國繪畫研究的“雙峰”,在于他們很早就開始各自探索如何建立中國繪畫的“歷史”。方聞的努力最早體現在《心印》一書中,由山水畫的斷代分析切入。高居翰更不必說,他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撰寫中國繪畫的系列斷代史,并在1988年推出《中國繪畫史三題》(Three 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Chinese Painting)。放在這個大背景之中,我們會發現,在對《溪岸圖》的研究之后,石守謙開始較多地討論元代以前的山水畫,并且逐漸深化了“畫意”的研究思路。最終的成果,便是《山鳴谷應》這部為中國山水畫撰寫的特別的歷史著作。而方聞的《為什么中國繪畫是歷史?》一文中的最后一節,便是“走向中國山水畫史”。石守謙通過畫意與觀眾的角度對山水畫史的討論,似乎讓我看到了一種傳承和致敬。
與《山鳴谷應》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英國藝術史家柯律格(Craig Clunas)2017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繪畫及其觀眾》(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兩本書都不約而同地關注中國繪畫中的觀眾問題,似乎反映出一種新的趨勢,雖然兩者取向十分不同,也反映了不同的學術脈絡。簡單地講,石守謙意在“建構”一部歷史,而柯律格意在“消解”一部歷史。這恰恰是因為觀眾。我們每一個研究者,都只不過是歷史的觀眾,但又何嘗只想成為觀眾?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