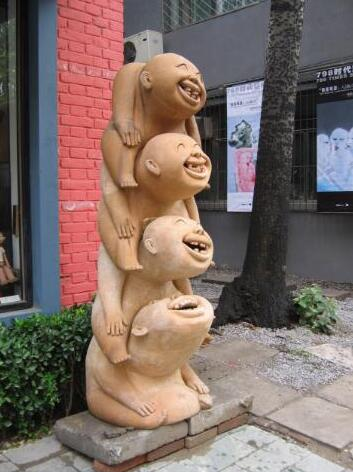
近日,申城某購物中心啟幕 “光域藝術計劃”, “為愛上色”墻繪再現陸家嘴……轉角遇到藝術,已經成為當下城市生活的常態。公園、廣場、街道、商場、地鐵站、機場,繪畫、雕塑、水體、公共設施……公共藝術的蔓延與拓展,似乎正在引領城市發展步入美學時代。然而,什么樣的公共藝術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在專家學者看來,公共藝術不能只有千篇一律、復制粘貼的炫酷視覺刺激。它需要考慮所處的地域環境,顧及公眾的感受,最終傳遞出一種獨特的、豐厚的精神價值。
——編者
大到草坪上的露天音樂廳,小到馬路上的下水道井蓋,沒有藝術抵達不了的地方,沒有創意滲透不了的角落時下,隨著人們對優美環境、愜意生活的向往與需求逐漸升溫,越來越多的藝術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走出藝術展館,走向城市的各個角落。它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公共藝術”。凝結著創意表現力的公共藝術,正在筑起一道道簇新的城市景觀。
近年來忙不迭巡展世界、儼然成為“網紅”拍照背景板的 “大黃鴨”,就是一件公共藝術作品,出自荷蘭藝術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之手。自2007年起,霍夫曼將經典的浴盆黃鴨仔造型放大數倍創作了一系列 “大黃鴨”。在藝術家看來,將事物擴大是為了讓人類個體變小、世界變小,如此一來,人們會感覺在作品面前消失,這種感覺恰恰可以讓你重獲自由,自由地去觀察、思考、暢想。到底真有這么回事還是牽強附會的說辭,其實挺難說。可以肯定的卻是,這只可親可愛的鴨子在藝術與普羅大眾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梁,打破了藝術界的某些權威性和莊嚴性,把藝術從美術館的殿堂中釋放出來,與城市、環境融合在一起,給予觀眾更加獨特與豐富的體驗。
因為一連串 “腦洞”頗大的公共藝術作品,美國芝加哥千禧公園舉世聞名。比如這座公園里的露天音樂廳,其實就是一座巨大的戶外雕塑,纖細交錯的不銹鋼結構在大草坪上搭起網架天穹,營造出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公共空間。同樣坐落于公園之內的皇冠噴泉,也與人們想象中的噴泉樣式相去很遠。它儼然一件以燈光和圖像來實現千變萬化的現代藝術品,不僅會噴水,還會“變臉”,將1000多位芝加哥市民的臉利用現代技術投射在15.2米高的LED屏幕上,營造出噴泉從他們口中噴出的幻象。更不用說這座公園里看起來像“不銹鋼豆子”的雕塑 《云門》,它曾被《時代》雜志譽為 “游客磁鐵”和 “非凡的藝術品”。英國藝術家阿尼什·卡普爾以液態水銀為靈感、用不銹鋼拼貼而成這件作品,恰可映射出漂浮的白云和摩天大樓的倒影,這是芝加哥的城市輪廓,所有的映像又都會因雕塑橢圓的外形扭曲而富于趣味。
等車時,候機時,不妨放下焦躁的心情,與身邊的藝術從容相逢。芬蘭藝術家安基斯雷巴創作的兩件動態裝置作品 “雨之舞”,不期成為新加坡樟宜機場的新地標。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動態雕塑,每件裝置占地39.2平方米,由608顆雨點形狀的銅珠組成。在后臺計算機的控制下,每個雨滴都可以單獨上下移動,每15分鐘變幻出16種不同的形狀和構造,從抽象的藝術造型,到栩栩如生的飛機、風箏、熱氣球,甚至是龍的形態。這樣的雨滴營造出嘆為觀止的視覺觀感,也給人們帶去一份心靈上的寧靜。
幽閉陰森、讓人一刻不愿多待的地下停車場,也可以借由藝術而絢爛起來。前段時間在法國某個地下停車場里,一位阿根廷藝術家完成了一件公共藝術項目,用丙烯酸涂料覆蓋了約2平方公里的混凝土,以大膽的幾何形狀拼接與混搭的色調鋪設了整個墻壁和地面。藝術家有意賦予原有環境中每個元素以新的功能,將空間變成一個巨大的雕塑,使得人們擁有在藝術作品內部呼吸的可能性。
就連廣告牌、斑馬線、垃圾桶、郵箱、下水道井蓋、路燈、長凳、電話亭之類的城市細節,都可以經由藝術化的改造化平凡為神奇。看,世界各地針對下水道井蓋的涂鴉藝術已經形成一股熱潮,或圓或方的井蓋上,幾筆隨意的涂抹就讓一個個生動的畫面呼之欲出。比如巴西圣保羅街頭的井蓋涂鴉走的是“萌”系路線,讓啃著魚骨頭的小貓、叼著肉骨頭的小狗、想吃奶酪的小老鼠等卡通形象裝點路面。意大利米蘭街頭的井蓋涂鴉則潮范兒十足,拿來棋盤、圖騰、抽象畫等諸多元素。藝術化的下水道井蓋不但成為美化市容的幫手,也以搶眼的視覺提醒雨中人留意它們的存在。
我們需要的公共藝術,不是把藝術品從展廳搬到公共空間,而是充當著公眾精神狀態的形塑者或城市創意活力的催化劑。
展示形式上從平面到立體,藝術功能上從點綴性到實用性,公共藝術似乎有著廣闊的外延。然而,在專家學者看來,優秀的公共藝術其實也總有著某些特定的內涵,不是把藝術品搬到公共空間就行。它們以一種空間上的開放形態與公眾、與環境相融,影響著公眾的精神狀態,也催化著城市的創意活力。
英國利物浦北部克羅斯比海灘上的景觀裝置作品 《別處》,就是不少人眼中的經典案例。這是英國雕塑家安東尼·葛姆雷以自己為模特所澆筑的100座真人大小鐵制雕像。1997年起,它們被置于三公里長、一公里寬的海灘上,隨著潮起潮落、地勢起伏,人像時隱時現,感受著大自然的美景與輪回。測試時間和潮水,靜止和運動,并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到海灘的日常生活中,是創作者的初衷。漸漸地,這件公共藝術作品還被人們賦予某種象征意味——這片海灘是遠赴美國的移民看到的英格蘭最后的一片風景,當年數百萬的人們就是從利物浦啟程前往新世界的,因而 《別處》又像是一座紀念碑,讓遠離故土的人們在懷舊的同時感到希望的力量。
位于西班牙巴塞羅那的北站公園,算得上一件超大型因地制宜的公共藝術作品。占地2.2萬平方米的這座公園,是巴塞羅那為了1992年奧運會,由原來的北火車站改建而成的。兩個具有明顯差異甚至是互補的元素——太陽和陰影,構成了它的主體。其中,太陽區域安放的是 “沉落的天空”,大量不規則陶瓷釉面砌成的藍色雕塑宛如海浪,通過反射形成天與地的和諧對話;陰影區域安放的是 “旋轉的樹林”,將樹木作為景觀的組成部分,運用季節的變化形成豐富的景觀變化。雕塑成為公園的同時,公園也成為了雕塑,它們互相融合,共同詮釋著巴塞羅那這座地中海城市的特質,某些元素甚至有著致敬這座城市的藝術大師——安東尼奧·高迪之意。
恰當的公共藝術作品,當真能夠將某種積極的氛圍傳遞給公眾。有一年的情人節前后,紐約時代廣場上一件名為“BIG誙NYC”的心形互動裝置作品,利用廣場的人流、空氣和觸摸啟動讓來來往往的人群感受到了暖暖的愛意。這件高3米多的作品,用四百根透明亞克力管組成了一顆巨大的愛心,它所折射出時代廣場上的熠熠燈光,則圍繞著心形形成一圈光暈。隨著塑料管在風中搖曳,懸浮的心呈現出脈動的感覺。當人們觸摸這個心形感應裝置時,人的能量被轉化成更多的光,愛心會變得更亮,跳動得更快。
同樣是游走全球的公共藝術,來自紐約藝術家科特·波希克的 “大紅球”在不少人看來比 “大黃鴨”來得高明。這真的只是一只直徑約4.5米、體重約113公斤的大紅色充氣圓球,簡單得有點笨拙。它總是出現在人們意想不到的地方,或塞在兩幢建筑中,或堵住博物館的大門,或乘著河上的游船,每個特定的位置只持續一天。顯然,這只大紅球的意義不在于它的形態本身,也不在于它真的身處何處,重要的是它所帶來的象征意義——它是一個俏皮且富于魅力的切口,源源不斷地激發著人們的想象力,調動起人們的參與度。藝術家曾坦言: “大紅球周游世界時,各地的人們都會來和我交談。每一次一個行人路過,都會說,你知道嗎,我知道有一個地方非常適合放這個球。”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