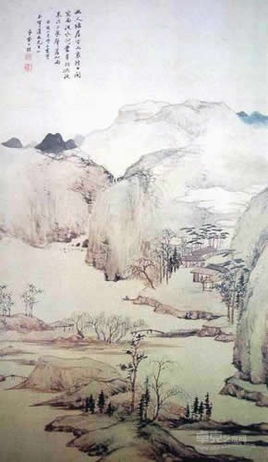
據姚翁望《安徽畫家匯編》統計,明清以來,徽州畫壇涌現出767位有成就的畫家。除了被稱為“新安四家”的:弘仁(法名)、汪之瑞、孫逸和查士標,還有鄭旼、祝昌、姚宋、江注等,他們的成就共筑起了新安畫派。當然,新安畫派的興盛也決不是偶然現象,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徽商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賈而好儒,好藏宋元名跡
任何畫家的成長都離不開對前人藝術成果的學習和借鑒,這樣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精進。明清時期,宋元名畫尤其是元末著名畫家倪云林、黃子久的畫作,是畫家都喜歡觀摩、學習的寶貴資料。那時沒有博物館、美術館,藝術品的公共性無從談起,名貴的書畫要么被巨賈之家收入,要么流入當朝內府。徽商富有,人所共知,“賈而好儒”,又是一大特色。他們對于前代的藝術瑰寶具有濃厚的興趣,也有優厚的資本購買珍藏。
當然這種風尚的形成也受到了當時徽州官員士大夫階層的影響。明末商人吳其貞在《書畫記》中說:“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其風開于汪司馬兄弟,行于溪南吳氏,叢睦坊汪氏繼之。余鄉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榆村程氏,以得皆為海內名器。”這里所說的汪司馬兄弟,指汪道昆、汪道貫。汪道昆,官至兵部左侍郎,尤其喜愛收藏古董字畫,登門求觀的文士絡繹不絕。他的行為不能不影響眾多的商人,乃至形成這樣的風氣。因此,好儒崇雅的徽商收藏古玩也就不足為奇。
徽商憑借自己富甲一方的雄厚經濟實力,收藏了大批宋元時期的法書名畫。據吳其貞描述,他在程季白之子程正吉家中看過王維、趙孟頫的手卷和荊浩的立軸山水,以及其他一些書畫作品。如王維的《江山雪霽圖》手卷、李唐的《晉文公復國圖》、翟院深的《雪山歸獵圖》、趙孟頫的《水村圖》手卷,還有書圣王羲之《行穰帖》的唐初摹本等。
近代歙人黃次蓀(崇惺)在《草心樓讀畫記》中談道,徽商收藏名家作品之多,令人驚嘆。如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吳道子的《黃氏先圣像》、閻立本的《孔子事跡二十四圖》、李龍眠的《白描十八應真渡海長卷》等。而當時的“休、歙名族,乃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是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名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與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鑒賞家所津津樂道者”。這些“休、歙名族”之中,有“弆藏法書名畫、金石文字、鐘鼎尊彝甚夥”的歙人巴子安,大鹽商汪廷璋的侄子、“家蓄古人名畫極富”的汪灝,基本上都是徽商。
徽商的收藏更給當時的藝術市場增添了巨大活力,“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這導致很多書畫古玩精品匯聚徽州,使這里成為當時全國最有影響的收藏地之一,被后人譽為“文物之海”。當然,將藏品斂入深閨、束之高閣并不是徽商的做派,只要遇有內行知音前來,他們也展其所藏,供大家鑒賞、學習,乃至評判。據黃次蓀回憶:“諸先生往來其間,每至則主人為設寒具。已而列長案,命童子取卷冊進金題玉躞,錦贉繡褫,一觸手,古香經日不斷,相與展玩嘆賞,或更相辯論,龂龂不休。”畫家們在“展玩嘆賞”“更相辯論”的過程中,實際上就是在總結前人的經驗,吸取前輩的營養,這對于一個畫家的成長是大有裨益的。
新安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休寧查士標,“家多古銅器及宋元人真跡,書法華亭,畫初學倪高士(倪云林),后參以梅花道人、董文敏”,后人評價他的畫作“直窺元人之奧”。之所以如此,與他從元人畫作中汲取豐富的營養是分不開的。新安畫派首領弘仁“聞晉唐宋元名跡,必謀一見”,傳移摹寫,認真研讀。他與徽商吳羲私交甚好,常在吳家賞閱古代大師的作品。吳家藏有倪云林的《幽澗寒松圖》《東岡草堂圖》《汀樹遙岑圖》《吳淞山色圖》等,弘仁見后,如獲至寶,苦心研讀達數月之久,藝術境界大大提升,回去后將自己過去的作品全部撕毀。周亮工《讀畫錄》認為其“喜仿云林,遂臻極境”。
為什么新安畫派推崇“元四家”“宗向倪、黃”?其根源應從畫壇的“南北宗”論談起:明代畫家董其昌從儒、釋、道的哲學體系出發,將過去的文人畫家分為南北二宗。北宗畫家多為皇親貴戚及畫院職業畫家,南宗畫家為僧道、隱者、亦仕亦隱者。董其昌推崇南宗,倡導倪畫,對中國畫壇產生較大的影響。使南宗的審美思想和藝術追求成為明清畫壇的主流。倪云林是南宗的代表人物,又是新安畫家學習的榜樣。他散財棄家,過著“欲借玄窗學靜禪”的隱逸生活,與新安派“棄舉子業”,皈依釋道,在哲學思想和審美追求上自然不謀而合。
徽商受此社會風尚的影響,為推崇風雅,便以收購倪畫為榮,家藏倪畫為高,促成了新安畫家皆宗倪畫的風格。面對散盡家產、浪跡江湖的倪瓚,與其繪畫中清淡簡勁、冷靜瘦峭、枯寒雅逸的獨特氣質,這些生于黃山腳下,處于改朝換代之際的遺民畫家,在情懷上怎能不一拍即合!
好客尊士,經商作畫交游
畫家成長,畫派形成,離不開師友之間的切磋、交流,徽商的好客尊士恰恰為畫友間提供了良好的交流環境。“賈而好儒”的徽商與文人學士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共同的愛好產生了許多共同的語言,優厚的待遇又吸引了大批書畫名家及各界名流蜂擁前來。
當時的揚州是徽州鹽商的聚集地之一,他們在揚州建有大量園林,優雅清靜的環境成了書畫名家、文人學士切磋交流的理想之地。故時人說:“揚州書畫(家)極多,兼之過客往來,代不乏人”,這些來揚州的文人學士,大多坐館于某一大鹽商之家,或成為某一鹽商的座上賓,受到了鹽商的優厚禮遇。乾隆年間,歙縣汪廷璋購得揚州名園——筱園,人稱汪園,有史料稱:“自其先世大千遷揚州以鹽筴起家,甲第為淮南之冠,人謂其族為鐵門限……守財帛富至千萬。”
此外,汪廷璋還花重金延聘名家于座中,作畫示范,教授他人。如歙縣畫家方士庶,“早年畫山水,運筆構思,天機迅發”,中年投奔汪廷璋為其門下客,“時令聞(汪廷璋,字令聞)以千金延黃尊古于座中”,方士庶得以師從學畫,“以是士庶山水大進,氣韻駘宕,有出藍之目”。終于成為新安畫派的重要人物。浙江畫家張洽,“工山水,有大癡神理。晚年買山棲霞,畫家多從之游”。他也是汪廷璋的座上客。汪廷璋的侄子汪灝,也工詩畫,為了進一步提高技藝,汪家特用重金將張洽“延之于家,結為畫友,由是右梁(汪灝,字右梁)山水氣韻大進”。
徽州鹽商江春與其從弟鹽商江昉同樣在揚州聲名顯赫,富稱一時。江春建有隨月讀書樓、康山草堂,江昉建有紫玲瓏閣,專以留居名流學士。他們的好客尊士,吸引了大批詩人、畫家、學者,“一才一技之士望風至者,(江春)務使各副其愿”。據《揚州畫舫錄》卷12載,江春的座上客,有姓名可考者達50余人。江春死后,“泣拜于門不言姓氏者,日十數人”。如浙江陳撰、許濱翁婿兩人就同時坐館于江春家。儀真人積兆熊,晚居隨月讀書樓,他不僅工于詩詞,而且書畫也精,“畫筆與華喦齊名,書法為退翁所賞”。還有新安畫派的重要人物程邃,歙縣人,號江東布衣,又號垢道人,查士標評價其畫:“鐵筆之妙,直逼秦漢,其蒼老輕秀之姿,遠過前人,人得之寶為拱璧,間乘興作畫,寫胸間磊落之氣,深得摩詰(王維)神理。”他晚年也僑居江都。
除了“會畫友”,畫家的成長還有賴于“廣交游”。要做到這一點,沒有雄厚的經濟條件作支撐,是無法想象的。新安畫家中也不乏出身徽商世家,甚至自己一邊經商、一邊作畫的人。如查士標,“家多古銅器及宋元人真跡”,為了提高畫藝,又“延王石谷至其家,乞潑墨作云西、云林、大癡、仲圭四家筆法,蓋有所取資也”。前述巴子安,“能畫山水花鳥,皆工”,其“家豐于財”,顯然也是一個商人家庭。歙縣畫家吳云,“其父賈人也”,家庭比較富有,從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初師許南村,年十四,父親“挈去入浙,命習會計,不屑,俾掌刀布(錢財),耗且盡”。父親去世后,留下一筆遺產,于是他“走京師,從某貴人作塞外游,日與文學士俱,遂工詩畫”。如果他沒有商人家庭的經濟支撐,是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畫家的。類似情況還有孫嘉駒,也是徽州人,“以鹽業為錢塘諸生”,后來僑寓臺州之樂城,“善畫工詩”,其畫作并收入《兩浙名畫記》。
更有一些徽商,工詩且善畫。如江昉,“善寫生,于秋葵為最工”。江振鴻,是大鹽商江春的嗣子,本人也從事鹽業經營,寄籍揚州,“性好客,家有康山園(即康山草堂),海內名流至邗江者,必造焉,流連觸詠,殆無虛日”。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江振鴻學業大進,時人評價他:“善古文詞,工草書,又善山水花卉,皆精妙”;“山水(畫)不減衡山(文徵明),花草(畫)不減白陽(陳道復)”。
刻書制墨,光大徽派版畫
論及新安畫派的形成和發展時,我們不能忽視其他畫種尤其是徽州刻書業和制墨業對其產生的影響。這兩種文化產業或者就是徽商經營的,或者與徽商有著密切的關聯。
明清時期,徽州地區從事刻書業的工人數量多。除了印刷、校審質量高,美輪美奐的版畫插圖更是徽州刻書的特色之一。這些插圖要靠專業人士創作,這就為畫家提供了展現才華的舞臺。如丁云鵬(繪《宣和博古圖》《養正圖解》)、吳逸(繪《古歙山川圖》)、汪耕(繪《人鏡陽秋》《北西廂記》)、程起龍(繪《女范編》)、梅清(繪《黃山志》)等。更為著名的插圖書籍,初期要數嘉靖間黃鐘所刻的《文房圖》。隆萬大改革時期以后,徽派插圖本圖書更顯精工富麗,漸漸形成獨特細膩、大膽潑辣的藝術風格,世稱徽派版畫。受此影響,新安畫家的風格多是線條剛勁有力,造型簡潔明快,明顯有著受版畫影響的痕跡,特別在漸江、丁云鵬的畫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徽州刻書與徽商又有什么關系呢?很多徽商家庭,喜讀書、愛藏書,對纂修譜牒高度重視,市場需求急速增大,甚至有商人直接投資,把徽州刻書業推向鼎盛階段。例如號稱“四元寶”的徽州大鹽商黃晟、黃履暹、黃履昊、黃履昴四兄弟在業鹽的同時就投資刻書業,刻成類書《太平廣記》《三才圖會》《圣濟總錄》《葉氏指南》等書。
據居密(美)、葉顯恩統計,明清時期,徽州的家坊、書坊有近四十家,其中大多為商賈。長期與市場打交道的徽商,形成了十分靈活的經營理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擴大,徽商介入刻書業后,充分考慮到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需要,如童蒙書籍、戲曲、小說、醫書、商書、廣告圖書紛紛出現。在這個過程中,為增強書的可視性、可讀性,書商們干脆把繪畫藝術與刻書業結合起來,有的索性將新安畫家的畫作用木版印刷出版,如孫逸《歙山二十四圖》、弘仁《黃山圖冊》都曾用木版印刷出版。
至于徽州墨商對新安畫派的影響,主要是新安畫家參與了墨譜設計和圖案繪畫。制墨徽商為提升墨品文化品味而加強制墨工藝的研究和對外宣傳,特延請畫家為其墨模繪制山水、人物、花鳥等圖案。其中墨商程君房和方于魯尤為突出。程氏曾特聘畫家鄭重及雕刻名工黃鏻、黃應泰諸人,聯手繪刻了《程氏墨苑》,其譜分玄工、輿圖、人宮、物華、儒藏、錙黃等六類,又析分上下,是中國古代藝術水平最高的墨譜圖集。程氏在墨的造型設計和圖式安排上新意迭出,丁云鵬的圖稿精麗絕倫,黃氏三匠的刻工勾凝斷頓,線條細若胎毛、柔如絹絲,曲盡其妙。著名畫家的精心設計,技藝高超的畫工的配合,使《程氏墨苑》成為中國版畫史上少有的精品。鄭振鐸曾說:“余收版畫書20年,于夢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從《十竹齋箋譜》及初印本《十竹齋畫譜》。”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徽商的商業活動為藝術家們施展才華,提供了舞臺,是徽州藝術得以發展興盛的原動力。他們資助興辦文化、教育,熱衷收藏,才會有新安畫派的勃興。徽派版畫和新安派繪畫間,相互汲取營養,相互影響,成為中國繪畫史上兩朵美麗的奇葩,徽州商人功不可沒!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