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來了,開了一槍”
“夏展”(Summer Exhibition)一直是英國皇家學院每年掛歷上的盛事,自1768年夏天開展至今,已連續舉辦248屆。這是面對公眾開放接收作品的最古老的展覽之一。
夏展由Varnishing Day開始(Private View),畫家們往往會在這一天來到皇家藝術學院的展廳里,審視一下別人都展了什么東西,給自己的作品添加最后幾筆修改,迎接一周之后面向公眾正式開放的日子。
1832年的Varnishing Day,有一次緊要的擦槍走火。 那一年的夏展焦點,是皇家學院兩位院士:康斯特博(John Constable, 1776-1837)選擇展出作品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對面掛著透納[ 朱光潛在西南聯大講英國美術史,說:“在透納之前,泰晤士河上不曾有霧”。](JMW Turner, 1775 – 1851)的Helvoetsluys。在V Day這一天,康斯特博早早來到皇家藝術學院依然伏在畫布上,仔仔細細用他獨特的“Constable Snow”的技法(一種反復、頻繁點出的白色顏料,在觀者離畫作有一定距離的時候,可以用來模擬人看到的反光)來修飾新橋通車當天的盛景。

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 John Constable, 1817。 Tate Britain, London。
稍后不久,透納也慢慢悠悠來到皇家學院的展館。后來的故事因為被電影《透納先生》拍了出來而被大家所熟知,我在此復述一遍,因為關系到我們后面文章的展開:
透納進了展廳里,和康斯特博互相問好。趴在Helvoetsluys畫布前,在一片陰云和風暴中,在海面點了一個鮮紅的浮標。

JMW Turner putting on a finishing touch on Helvoetsluys, film clip。

Helvoetsluys, JMW Turner, 1832。 Fuji Art Museum, Tokyo
透納畫完這一筆,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展廳[ 電影里他對眾人不屑地唾了一口,很神氣。我沒有找到相關的文獻記錄這個行為。],剩下康斯特博站在那里,筆掉在底地上,臉色慘白地站著發抖。聽到聲音的其他院士們紛紛趕來這間屋子,問康斯特博發生了什么事。康斯特博指著透納的畫說:“他來了,開了一槍。”(He’s been here, and fired a gun)。
康斯特博如此震驚的這“槍”打在哪里,我們可以猜測:一個浮標巧妙降低了整幅畫的重心,讓場景在觀者眼里更為宏大(觀者成為了仰視)。加重了風暴中渺小而搖曳的無力感,或者可能只是一個鮮艷的層次,讓觀者在宏大的敘事中有了一個可靠的抓手,一個安放視線的有效前景。
畫家之間的競爭,在夏展尚未開幕就是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 人們感興趣的印象派畫家,似乎卻不存在這個問題,總是表面上一派和氣,集體展出。可能也是因為當時的社會對他們一并敵視,反而促進了他們之間的情誼。雖然莫奈和德加也并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展覽。康斯特博和透納,彼此之間總是透著一種“既生瑜,何生亮”的敵視。印象派畫家之間是沒有的:他們都覺得自己是沒有周瑜的諸葛亮。莫奈不喜歡和雷諾阿一起出去寫生,覺得雷諾阿會抄他的作品。德加不喜歡和印象派一起展覽,他覺得自己不是印象派。當然,這是后話。],似乎是貫穿二百年歷史的核心主題。在今年皇家藝術學院的夏展中依然可見。作為全世界最古老的面向全社會接受展品的展覽,今年皇家藝術學院的80位院士評委要從一萬多幅來自社會各界的畫作中挑出1250幅進行展覽。皇家學院成立夏展的初衷,就是給當時沒有辦法展出自己的作品的社會畫家們一個展覽的舞臺。直到今天,這一傳統依然延續了下來。畫家和雕刻者們,每年都背著自己的作品來到皇家藝術學院的門前,已經成名的院士和藝術家,帶作品來展示自己的新思路和創作的新方向。而還沒成名的年輕人,剛入門的藝術愛好者,則更希望能被人們記住,像康斯特博說的:“他來了,開了一槍。”
“Artistic Duos”
今年的夏展,由Richard Wilson院士策劃,聚焦于以雙人創作為主的藝術家群體(‘artistic duos’)。這一側重點也讓不少評論家傷透腦筋: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為什么兩個人一起創作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那三個人呢?五個人呢?十個人呢?
兩人創作的主題也沒有明確地體現在展覽之中,畢竟最后展出來的展品,藝術家依然強調并注重了一定的和諧(coherence),在構思層面和執行層面,都看不出任何兩人創作比之一人創作的獨特之處。

今年的展品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由Ian Ritchie和Louisa Hutton布展的Artchitecture Room。兩位院士決定以藍色刷墻,將整個空間壓縮,并且讓背景對視覺造成的疲勞減到最小(是一件必要的工作,考慮到展品的精細)。今年的主題是“Unbuilt”,布展突出了那些沒有被實現的建筑構思和理念。在介紹中,兩人就直言太多年輕的建筑師發現在這個行業里立足已經越來越難,因為最終實現創作理念所需的資源和金錢投資都意味著只有相當小的一部分建筑理念會最終被實現。所以今年的建筑單元聚焦于那些“藏于草稿本和柜櫥里被人遺忘”的設計。
同時展出的,除了年輕建筑師沒有實現的想法,還有其他一些成名建筑師的最終沒能與世人見面的理想:有些是參加競賽輸掉了沒有人投資,有些是因為經濟環境改變,有一些則單純超出了他們所在的時代太遠。
六號展廳是此次展覽的另一個亮點:探究藝術在對一個充滿動蕩和戰爭的世界所起到的愈合作用,以相片和雕塑為主要載體陳列出來。日本藝術家青野文昭的作品尤為引人注目。他使用在2011年3月日本海嘯之后從廢墟中尋找到的物品,將破碎的物品重新構建出完整的可認得藝術形式,體現了“愈合”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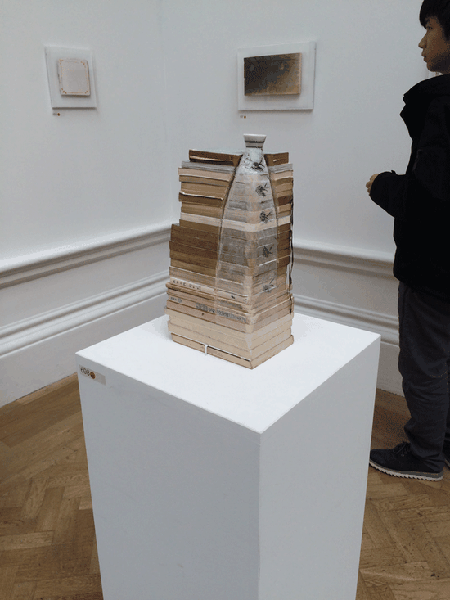
六號展廳的介紹中,突出了“創造”和“摧毀”這兩個主題。巧的是,這似乎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價值的兩條線索。從兩次世界大戰中誕生的數個流派(解構主義、達達主義、存在主義),都是以“摧毀”為手段,以“創造”為目的。通過解構權威而實現自我。二十世紀隨廢墟誕生,創作似乎也過于癡迷于打破,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首先提出作者不是作品的最終解釋,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提出人們不應該在作品中尋找熟悉的日常體驗。人們在一百年間,把創作從“涵義”(meaning)中解放出來。然而解放出來之后,人們依舊在原地留守,要去哪里?似乎也是沒有人可以確切地說出來。
似乎是“我與廢墟纏斗過久,我也變為廢墟。”
“天啊,一切都太復雜了”
夏展一直以“當代藝術”為主題,給先鋒藝術創作一個發聲空間。“當代藝術”作為一個定義寬泛的詞,在這里的使用似乎十分不妥。在一個高度上理解,就是“所有活著的人創作的被活著的人嫌棄的藝術”的簡稱。自從印象派誕生以來,當代藝術“被嫌棄,興起,被嫌棄,被接納,被嫌棄”的輪回就是藝術史中的一個重要的生命力。如果一個人沒有嫌棄過當代藝術,似乎就沒有參與過藝術史。早在19世紀,德加在看到他不喜歡的當代藝術被拍出高價的時候,也曾默默說了一句:“有些成功和恐慌并無二致(There is a kind of success that i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panic)”

也是因為夏展對先鋒藝術的追求,歷年來,人們給予夏展的評論,和人們給予當代藝術的評論并無不同。作家Stephen Fry在2010年夏展的晚宴上作為開幕嘉賓,曾經公開講述類似的疑惑:
“… 我們應該理解這些畫嗎?我們在看展時應該交談嗎?我們應該完全安靜,站在畫前面,瞪著它看,并不對人揭示我們的感受,還是我們應該偶爾非常大膽,說我們喜歡這個表達方式,那個形狀,或者那些顏色?
我們是否應該模仿那些站在另一邊大聲炫耀自己有許多知識,用著“morbidezza” “sfumato[ 暈涂法,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繪畫技藝。]” “golden sections”這些詞語的人?我們如果不喜歡這樣的人,是不是我們太自大了?他明顯在欣賞并享受這些畫作,還與他的同伴帶著熱情和知識分享他的感受,這似乎沒錯?我們為什么假設他在炫耀?這假設,是不是揭露了我們自己的不安全感?我們是不是應該對我們面前這幅大師的杰作展示一些不喜,反而去喜歡那些沒有名氣的人的作品,來體現我們懂得如何鑒定作品的原創性和不被名聲所欺騙?
天啊,這一切都那么復雜(Oh dear, it is all so complicated)”
每一年的夏展,都會引來同樣的爭議,混亂和困惑。《每日電訊報》在2015年對夏展的評論尤其尖刻,說夏展是“高端垃圾場(high end junk shop)”《每日電訊報》還引用1949年的夏展時皇家學院的主席Alfred Munnings說的一番話:“如果我在街上看到畢加索,一定會過去踢他一腳:‘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你畫一棵樹,就畫的像一棵樹吧’”
不可置疑的是,如今的皇家學院,從“那個畫一棵樹,就畫的像一棵樹”的理想里已經走了很遠了[ 20世紀過后,人們把畫什么像什么這個常識稱為“自然主義”,“超寫實主義”等等]。這也似乎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畢竟畫一棵樹,如果就像一棵樹的話,很多藝術評論家也就要失業了。藝術評論家,自夏展開始之際就巧妙融入,把自己變成了夏展的一部分。 比如1881年,參加夏展開幕式的時候那些小姑娘們,都帶著崇拜的表情等王爾德解釋這些藝術品的來龍去脈[王爾德雖然給妹子們講畫,他自己卻是反對art criticism:“What is the use of an art critic?。。。 Nowadays, there are so few mysteries left to us that we cannot afford to part with one of them” (The Critic as an Artist, Part I)]。

A Private View at the Royal Academy, 1881, William Firth。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每日電訊報》的詰問,反映出了藝術的發展的一個副作用:評判標準的消失。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一百年,文學界和藝術界從廢墟中成長起來,帶著傷痕開始的一代人,開始像生活中被摧毀的一切看齊,在創作中摧毀權威。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畫(Old Masters)的標準被認定不能再用了。突破意味著拋棄標準,而新的標準的建立卻遲遲缺位。也不得不說是一個至今依然遺憾的事情。2014年,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刊文《當代藝術依賴金錢標準而非美學價值》[ “Contemporary art is judged by its price tag, not aethestics” 金融時報2014年11月18日刊]討論這一問題,文章中悲觀地指出,我們已經集體失去了以美學標準判斷藝術品的能力,而只能覺得“越貴越好”。我們看重潮流,價簽,以及最流行的噱頭,而不是藝術品本身。
然而金融時報這篇痛徹心扉的文中,那位作者也不能免了自詰一句:哪個年代不是呢?
結語
我坐在RA旁邊小咖啡館的落地窗旁邊,敲敲打打這篇評論。身邊都是剛從夏展出來的人,看見我在敲打,大概也都猜到了我在做什么。對面有個姑娘,敲敲打打,是不是一樣的事。
一百七十年前,波德萊爾給1846年的沙龍夏展寫評論,他說:
“評論者是幸運的,他沒有朋友,這是他最大的優勢,他也沒有敵人。
我真誠認為,最好的評論,是娛樂而帶有詩意,而非冷冷的,分析性的評論。分析性的評論自稱解釋了一切東西,其實是:沒有了恨,沒有了愛,刻意地掏空了一切情感。
既然一幅畫是自然在藝術家心里的投影。那么我要說,一個最好的評論,是一幅畫在一個智慧而敏感的心靈里的投影。對于一幅畫最好的評論,甚至應該用十四行詩或者一首悲歌唱出。”
波德萊爾這話,桑塔格點頭同意:不要用智識(intellect)壓抑美(aesthetics)。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莊子,每一堂課都擠滿了人,第一節課,先生對學生們說:“莊子呵,我是不懂的咯,也沒有人懂”。
既然不懂,為什么還要撐著講?大概因為心里存著波德萊爾說的:對其有愛,有恨,也有一首悲歌。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