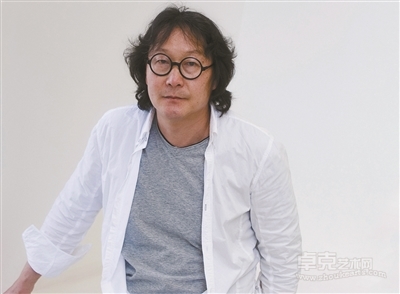
徐冰

鳳凰-2015

天書 The Book from the Sky 1987
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的2號展區(qū),意大利國家展的入口處,正在展出徐冰的大型裝置藝術(shù)作品《鳳凰-2015》。就在雙年展開幕前一天,威尼斯國際大學(xué)專為《鳳凰》召開了一場大拿云集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鳳凰—歷史的迷思”。
徐冰在海外的熱度與所受的追捧,顯然要遠(yuǎn)高于其在國內(nèi)的影響力。以英國為例,大英博物館、V&A博物館、牛津大學(xué)阿什莫林博物館等英國最頂級的博物館都已做過他的個人作品展。他還是由牛津和劍橋大學(xué)聯(lián)合建立的“藝術(shù)、社會與人文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劍橋大學(xué)東亞研究所教授方德萬(中文名)教授評價(jià):“徐冰的作品很發(fā)人深省,卻不失有趣,內(nèi)藏一種柔軟,而不是以直接、粗暴的方式面對觀眾。這種柔軟絲毫不減損其作品的力度、思想的深度。”
創(chuàng)作從未離開“漢字的方式”
不止一次,徐冰強(qiáng)調(diào)自己“是一個中國藝術(shù)家”。“我的文化、學(xué)識主要都是在中國奠定的,我創(chuàng)作的動力、思想和武器,得益于中國這個特殊文化背景。”徐冰1990年離開中國赴美時(shí)已35歲,非常成熟的年紀(jì)。從某種程度說,徐冰在去西方前,中國的文化基因確已在他身上完成了生長、發(fā)展、定型的過程。
“中國人的性格、思維、看事情的方法,審美態(tài)度和藝術(shù)的核心部分甚至生理節(jié)奏,幾乎所有方面,其實(shí)都和"漢字的方式"有關(guān)。”徐冰說。顯然,他認(rèn)同由現(xiàn)代語言符號學(xué)而發(fā)展起來的結(jié)構(gòu)主義觀點(diǎn)—文字與語言在最底層與內(nèi)核最深處起著結(jié)構(gòu)思維、文化與社會的作用。也正因此,徐冰對自己中國文化基因與文化身份的清醒自覺與維持,遠(yuǎn)超于其他“走向國際”的中國藝術(shù)家。事實(shí)上,文字本身,也反復(fù)地出現(xiàn)在徐冰藝術(shù)創(chuàng)作生涯中,不斷成為他創(chuàng)作的媒介,也是他作品里用來象征“文化”的一個符號與工具。
徐冰出國前,他對文字、符號與語言的認(rèn)知,更多是直覺式的認(rèn)知。語言符號學(xué)、結(jié)構(gòu)主義、解構(gòu)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那是他去美國后才接觸的名詞與理論。在他于國內(nèi)創(chuàng)作《天書》時(shí)(1987-1990),他更多是憑著一種對漢字的天生敏感與理解。他試圖通過改造文字這一“人們最習(xí)以為常的東西”,去阻截人“思維的慣性”,挑戰(zhàn)既有的觀念與秩序。這種刻意打破“慣性”、打破“流暢性”的手法,正與戲劇理論大師布萊希特的“間離戲劇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天書》一出,在各界引起震蕩。1990年出國前,《天書》被指責(zé)為“新潮藝術(shù)十大錯誤傾向的集大成”。而《天書》被徐冰帶向世界后,卻備受好評,至今仍常被世界各地博物館借展。這樣的經(jīng)歷也讓徐冰明白,正是他自己身上這種來自中國的獨(dú)特的東西,帶給西方藝術(shù)系統(tǒng)從未有過的東西,而有其獨(dú)特價(jià)值。
盡管徐冰再三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中國藝術(shù)家”身份,但不可否認(rèn),十八年的美國生活,不可能不在他身上留下痕跡。也許那個“用”是西方的,而“體”卻是中國的。就好像徐冰身上“混雜”的語言系統(tǒng)—做嚴(yán)肅的思維與表達(dá)時(shí),基本以中文為主,架構(gòu)了徐冰的思維主體;但穿插性的,英文的碎片又四處散落和鑲嵌在一個已然成熟的語言系統(tǒng)里。這構(gòu)成了徐冰的主要表達(dá)特點(diǎn)。
《鳳凰》的產(chǎn)生是社會給予的能量
徐冰的創(chuàng)作也曾經(jīng)歷過誤區(qū),他說有很長一段時(shí)間誤將藝術(shù)創(chuàng)造等同于智力活動。后來,經(jīng)過很多試驗(yàn),研究了很多同代藝術(shù)家的作品后,他發(fā)現(xiàn)智商絕不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的核心:“創(chuàng)造能量來源于社會能量,而不是智力。”
徐冰作品中的能量,正是來自于現(xiàn)實(shí)。從《天書》、《鬼打墻》到《煙草計(jì)劃》、《木林森(002745,股吧)計(jì)劃》以及最新的《鳳凰-2015》等等,無一不是針對現(xiàn)實(shí)問題的發(fā)言發(fā)聲。他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與現(xiàn)實(shí)中的問題才是藝術(shù)家最根本的靈感來源、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思維動力,“有問題就有藝術(shù)”。他自認(rèn)這套藝術(shù)觀很中國式,“深受社會主義藝術(shù)觀影響”:藝術(shù)源于生活,藝術(shù)高于生活,藝術(shù)還原于生活。
徐冰于2008年回到北京,“一個時(shí)代的轉(zhuǎn)折往往蘊(yùn)含著巨大的能量,今天的北京就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實(shí)驗(yàn)的現(xiàn)場。”生活的轉(zhuǎn)場,同樣也激發(fā)出了個人內(nèi)里巨大的能量,轉(zhuǎn)場,不可謂不是徐冰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法。
甫一回國的徐冰,創(chuàng)作了《鳳凰2009》。彼時(shí)的中國就是一個大工地,金碧輝煌的高樓大廈與條件艱苦而粗糲的施工現(xiàn)場并置,只有置身于現(xiàn)場才能感受到的強(qiáng)烈反差,讓他萌生了創(chuàng)作靈感:用現(xiàn)代建筑工地所產(chǎn)生的各種垃圾廢料以及工人的勞動工具,打造一對體量巨大、在東方文化里意喻美好圓滿的“鳳凰”。這里面,意涵很豐富,最核心的追問直指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從中國到美國,它廣受關(guān)注,最后去了威尼斯,即《鳳凰2015》,叩問關(guān)于“全世界的未來”之命題。
創(chuàng)作靈感來源于所有儲備甚至是雜念
思維的動力來自于現(xiàn)實(shí),靈感的發(fā)生則常常是瞬間。比如,當(dāng)年他在創(chuàng)作被稱為“光的繪畫”之《背后的故事》時(shí),直接觸動他的一個場景是在西班牙機(jī)場轉(zhuǎn)機(jī)時(shí)無意間看到的一盆植物,影子投射在毛玻璃上。這樣的場景此前不是沒見過,可并沒有給他觸動。而他在接受德國國家東亞博物館的個展之后,準(zhǔn)備“復(fù)原”當(dāng)年二戰(zhàn)時(shí)期被蘇聯(lián)紅軍拿走的一批中國古畫之后,就有了任務(wù)在身的“思維緊迫感”,這個場景連同他此前關(guān)于鄭板橋的竹、影論,以及所有關(guān)于光、影的有關(guān)信息發(fā)生了化學(xué)反應(yīng),讓他想到利用茅草、樹枝、麻袋等物品,以光影的形式作畫,從“魂”上再現(xiàn)那批遺失的東方山水畫。而“光的繪畫”這一形式,在藝術(shù)材質(zhì)與語言上,則對傳統(tǒng)的油畫、水墨畫等是一種新的突破。
徐冰也特別指出了藝術(shù)家性格、氣質(zhì)、心境等對藝術(shù)作品的影響,“這些其實(shí)都會反映在你的作品中,比如一個藝術(shù)家急于成名,那么他的作品往往可能會在選題上走那種trendy(時(shí)髦流行的)路子,或宏大主題,或用色鮮艷醒目,因?yàn)槿菀滓鹱⒁猓蝗绻粋€藝術(shù)家覺得自己太local(本地化),想要國際化,他可能會特別想在作品中掩飾自己的地域身份,采用一些看似國際性的元素……最后,你所有的心思,試圖引起注意、試圖掩蓋什么的企圖,都會被自己的作品暴露無遺。作品本身最誠實(shí)。”
我問徐冰,他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理性、感性的特質(zhì)與平衡問題,因?yàn)楹芏嗨囆g(shù)家或者很多人,都更傾向于把這兩個特性看作對立的特質(zhì)。徐冰說理性與感性在他身上是相互刺激的關(guān)系,一體的,不矛盾。在他看來,一個人的思維能力越強(qiáng),感受力可能就越強(qiáng),因?yàn)樗季S密度更高,能把感受到的東西更好地發(fā)酵、生成出來。感受性越強(qiáng)、越豐富、越細(xì)膩,則同時(shí)又可以不斷地讓人的思維能力延展。
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不免經(jīng)歷才思枯竭的時(shí)候,這個時(shí)候怎么辦?他回答:一個藝術(shù)家,不能太執(zhí)著,往往,藝術(shù)的新鮮養(yǎng)料來自于系統(tǒng)之外,不要太把自己當(dāng)藝術(shù)家,不要太把藝術(shù)當(dāng)回事兒。你一心想成為一個藝術(shù)家,卻反而容易局限在系統(tǒng)里,思想被擠得很局促。他引用了自己最愛的禪學(xué)大師鈴木大拙的一句禪語:“在沒有任何可供參照的條件下,佛才出現(xiàn)。”套用到藝術(shù)創(chuàng)作里,“只有你真正徹底干凈了,真正有價(jià)值的東西才會出現(xiàn)。”
生死不談只用作品說話
與那些酷愛談?wù)撋赖乃囆g(shù)家不同,徐冰并不愿做過多追究這個問題:“這些問題誰都會思考,但卻其實(shí)不用談,也沒什么解答,我覺得所有人都無法解答這個問題。就怎么想把時(shí)間用好、用掉,就可以。生命的過程就是,你證明自己存在過。”
不僅日常中他對生死的話題不太愿談,在作品中也甚少見此類事關(guān)人類終極主題的作品。唯有充滿東方禪味的裝置《何處惹塵埃》,探討了存在、物質(zhì)與精神之間關(guān)系的問題。對此,徐冰解釋說,“很終極的主題,關(guān)于生、死、墓碑、八卦、陰陽等等,我個人覺得都需要很慎重去觸碰,因?yàn)樗旧砭哂泻軓?qiáng)的指向性、符號性。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強(qiáng)的東西,藝術(shù)無法強(qiáng)過這個主題本身。”因此,他一般比較回避直接去說這些終極的、深刻的、大的命題。
最后,我難以免俗地問徐冰關(guān)于未來的創(chuàng)作規(guī)劃,對此,他的回答是:“其實(shí)你要做什么東西,不是你自己計(jì)劃出來的,而是隨著你的生命動力,當(dāng)回過頭再看時(shí),才知道,哦,原來我做了這些東西,然后藝術(shù)史家或自己才可能會反省,他為什么會做這些事情?并找出蛛絲馬跡。其實(shí),這是你的宿命和必然結(jié)果。”
已辭去中央美院副院長一職的徐冰,希望把有限之精力專注于創(chuàng)作本身。對徐冰而言,“美院副院長”這樣看似代表身份地位的頭銜,以及那一連串耀目的獲獎記錄,似乎都遠(yuǎn)不如他的作品本身更有意義。
作品本身會說話。






 皖公網(wǎng)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wǎng)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