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圖注:西班牙建筑大師高迪
成功者倫佐·皮亞諾是個精致的機會主義者,殉道者高迪是個笨拙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各自所在的那個時代的產物。
1926年6月7日,巴塞羅那剛通勤的有軌電車在Gran Via de les Corts Catalanes大街撞倒了衣衫襤褸的高迪,他正打算去做禮拜,路人認定他是個乞丐而不施援手,直到一個衛兵攔了出租車,將他送到收容窮人的醫院,奄奄一息的高迪沒有得到有效及時的治療。第二天,Sagrada Familia的牧師發現了他,這位將余生獻給Sagrada Familia(神圣家族)教堂建設的“上帝的建筑師”——高迪,拒絕轉院,堅持呆在窮人中間,最后以一種近似殉道的方式離開人世。
2015年3月底,第二十屆普利茲克獎得主倫佐·皮亞諾的回顧展在上海的PSA隆重召開。從入場排隊的人山人海的盛況可以預言這個意大利人斷然不會覆高迪之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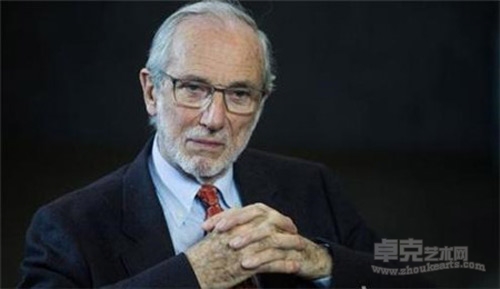
意大利當代建筑師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
高迪出生在巴塞羅那附近的小鎮,父親是個鍋爐制作工匠。年幼的他患有風濕病,他只能獨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靜觀”。哪怕一只蝸牛出現在他的眼前,他也能靜靜地觀察它一整天的時間。病養成了他緘默不合群的性格,還把他變成一個素食主義者,更培養了他對大自然的熱愛。
而倫佐·皮亞諾出生于意大利熱那亞一個建筑商世家,他的祖父、父親、四位叔伯和一個兄弟都是建筑商人,他從小就愛在工地上攀來爬去,對沙石變成房屋與橋梁驚詫不已,這奠定了他對建筑藝術與材料的崇敬。
高迪進入巴塞羅那建筑學校就讀,可是成績平平,盡管選過法國文學、經濟、歷史、考古和哲學,但他的主要興趣是在建筑,還因此掛過科。當高迪建筑學校畢業時,他的校長曾經說:“時間會說明我把畢業證書發給了一位天才還是一個瘋子。”
倫佐·皮亞諾畢業于米蘭理工大學,為Giuseppe Ciribin所賞識。之后在偉大的路易斯康手下工作過五年,在倫敦的馬考斯基工作室工作后,回到熱那亞建立自己的公司,他在開始國際化事業之前,就富有遠見地開始了國際化的經歷。
大富翁古埃爾是高迪這個孤僻內向、不愛交際的天才的保護人和同盟者。古埃爾既不介意高迪那落落寡合的性格,也不在意他那乖張古怪的脾氣。 “正常人往往沒有什么才氣,而天才卻常常像個瘋子。”高迪的每一個新奇的構思,在旁人看來都可能是絕對瘋狂的想法,但在古埃爾那里總能引起欣喜若狂的反應。高迪得到的是每個創作者所渴望的東西:充分自由地表現自我,而不必后顧財力之憂。
倫佐·皮亞諾的機會先是來自于日本人,后則來自于法國總統蓬皮杜,后者把蓬皮杜中心的設計賭博般交給了他和羅杰斯——兩個年齡四十不到的年青外國人,不過背后似乎有意大利承包商的影子。蓬皮杜中心是個歷史性的建筑作品,開創了所謂高技派風格。

高迪的杰作神圣家族(Sagrada Familia)教堂
高迪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無疾而終的戀愛。“為避免陷于失望,不應受幻覺的誘惑。” 高迪終生未娶。他把所有都奉獻給了建筑和宗教。高迪具有北歐人的外貌特征,金發藍眼。不了解高迪的人,認為他是個不善交際、令人討厭、言語粗魯而舉止驕傲的人,而他的親密朋友則認為他對朋友真誠,交流愉快,禮貌和友善。
高迪年輕的時候,一副花花公子的派頭,昂貴的外套、精心修飾的頭發和胡子,美食家,以及熱愛夜生活——時常乘坐馬車出沒在歌劇院和戲院。而當他年紀大的時候,依然留著大胡子,依然成天是一副陰沉沉、讓人捉摸不透的表情。但在生活上則變得極其簡單和節儉(他的吝嗇的名聲由此而來),他只說加泰羅尼亞語,對工人有什么交代就得通過翻譯。他只帶了兩個學生在身邊,多一個他都嫌煩。他似乎覺得,只要與這兩個學生交往,就能保持他與整個世界的平衡了。 他吃得比工人還簡單、隨便,有時干脆就忘了吃飯,他的學生只得塞幾片面包給他充饑。 他的穿著更是隨便,往往三年五年天天穿同一套衣服,襯衫也是又臟又破。有時真有人拿他當乞丐而給予施舍。

神圣家族(Sagrada Familia)教堂內部
相形之下,倫佐·皮亞諾總是滿臉微笑,看上去有些羞澀、溫和,像是個彬彬有禮的知識分子,卻善于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年紀輕輕就能夠偷偷把德國人的鋼梁用在法國人的蓬皮杜中心的工地上,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日本人、有錢的阿拉伯酋長和對西方殖民控制戒心重重的新喀里多尼亞的努美阿的土著長老們,對他都不是問題。
晚年的高迪失去了所有的重要的朋友親屬。而他自1883年主持的神圣家族教堂被當地人看成“石頭構筑的夢魘”,盡管因為得到教皇的高度贊揚,他本人也獲得了“建筑師中的但丁”的美譽,但因為經濟危機,教堂建設在1915年陷于停頓。高迪做了個驚人的決定,他回絕了所有業務,將自己的所有財產以及募捐來的善款,全部投入到神圣家族教堂的建設,對他而言,這個“窮人的大教堂”是他宗教理想和建筑理想合二為一的人生唯一工作。“只有瘋子才會試圖去描繪世界上不存在的東西!”
倫佐·皮亞諾的項目遍及全世界,建筑類型范圍也很驚人,從博物館、教堂到酒店、寫字樓、住宅、影劇院、音樂廳以及空港和大橋,還有愛馬仕的專賣店,他似乎無所不能。他宣稱“我屬于終其一生不斷嘗試新方法的那一代人,什么清規戒律、條條框框都不放在眼里,我們喜歡推倒一切重來,不斷地冒險,也不斷地犯錯誤。但同時,我們也熱愛我們的過去。所以,一方面我們對過去充滿了感激,另一方面又對未來的嘗試與探險充滿了熱情。因此我們乘風破浪,永無止息地超越過去。”其實,他連朗香教堂都不敢超越。

倫佐·皮亞諾設計的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
1926年6月12日,巴塞羅那萬人空巷為高迪舉辦盛大的葬禮。他被安葬在神圣家族教堂的地下室。這個教堂迄今沒有建造完成,成為宣傳巴塞羅那的巨大行為藝術。高迪在死后不久就被遺忘。1950年代,藝術家達利向世人呼吁重新認識高迪的價值。最后在1957年,MoMA(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美國著名現代藝術博物館)為高迪舉辦了回顧展。
倫佐·皮亞諾從沒在公眾媒體和學術媒體中消失過,自打蓬皮杜中心的巨大成功后,他幾乎獲得所有的重要建筑獎項,除了普利茲克獎外,還獲得了AIA金獎,丹麥的sonningpriseen獎。他是波黑的榮譽國民,是意大利的終身參議員,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親善大使,是年青人效仿的典范。
是時間證明了高迪是天才。他留下的是還在建造的教堂、“用自然主義手法在建筑上體現浪漫主義和反傳統精神最有說服力的作品”的米拉公寓和其他5個作品,被選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他最終在對建筑的執著、自然的深情、宗教的虔誠和加泰羅尼亞的熱愛中發現并成就了自己!
皮亞諾作品的識別標志是它們沒有識別標志。皮亞諾的傳記作者宣稱,倫佐·皮亞諾“對于那些排斥教條和主義的年輕建筑師們來講是一個榜樣和激勵,認為他的作品沒有浮夸的表情,透露出稀有而溫暖的人文精神,執著地關心著天空、大地和人的內心,總是顯得冷靜而清醒。” 有趣的是,盡管倫佐·皮亞諾之后設計了一系列叫好的建筑,但似乎沒有一棟的影響力和歷史地位超過蓬皮杜中心。
“沒有哪座城市會像巴塞羅那,因一個人(高迪)而變得熠熠生輝。”
熠熠生輝的倫佐·皮亞諾致力于保護熱那亞古城,卻沒有讓熱那亞熠熠生輝。
成功者倫佐·皮亞諾是個精致的機會主義者,殉道者高迪是個笨拙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各自所在的那個時代的產物。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