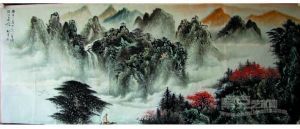
黎雄才八尺巨幅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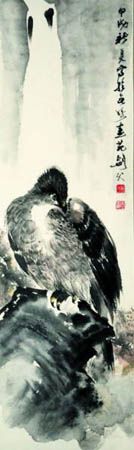
高劍父《秋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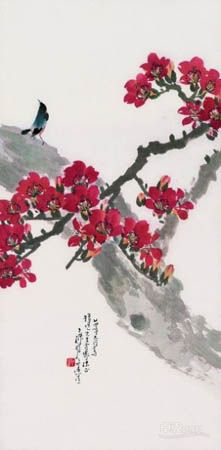
陳樹人作品
專題策劃 白嵐 余永堅 采寫 信息時報記者 馮鈺
嶺南畫派是否依然存在,這是一個值得探討、尚未得出結論的問題,但嶺南畫風卻毋庸置疑地風生水起。探討20世紀百年來的廣東美術,我們發現,在現代美術和當代藝術的發展過程中,廣東美術的百年流轉中有許多可以言說的驕傲。
上個月在廣東美術館舉行的“藝無涯陳大羽百年藝術展”全國巡展廣州站研討會上,與會的美術批評家們回顧了廣東美術近現代來的發展。雕塑家、中國美術協會會員錢海源說:“一部20世紀百年的中國美術史和廣東美術史,是和20世紀一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革與發展史同步發展的產物。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使封閉與落后的中國被迫開放,而廣東是最早對外開放、最早接受外來思想文化和藝術新思潮的地域。我認為,具體談到廣東美術與外來影響的關系,要上溯到更早的明清時代。在近現代中國美術史上,廣東美術家對中國近現代美術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是眾所周知和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可以這么說,一部近現代美術史,一大半是由廣東美術家書寫與創造的歷史。”
油畫和版畫
是從廣州傳入內地的
據《中國明清油畫》記載,油畫傳入中國發生在1579年即明朝萬歷七年。1582年8月7 日,喬瓦尼、利瑪竇和巴范濟等西方八名傳教士到達廣東澳門,開始在澳門學習中文和傳授油畫,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傳授西方油畫的美術學校。通過學校培養出來的油畫家,一是到全國各地去傳授油畫藝技知識;二是大批量臨摹繪制當時被稱之為“玻璃油畫”銷售到海內外;三是從中產生一大批像關喬昌那樣的聲名卓著的嶺南油畫家。關喬昌所留下的作品很多,包括人物肖像、嶺南風俗和風景畫。在藝術上可與西方油畫媲美,名聲遠播歐美。1594年左右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將部分油畫和四幅銅版畫作品帶入北京,也許這是中國人在本土上初次見到銅版畫。自鴉片戰爭《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簽定后,不少廣東油畫家北上發展,當時有位名叫周呱的廣東油畫家,就是“海派油畫”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從而使中國內地的油畫才開始活躍和發展起來。
中國最早到西方留學、學習西方藝術的人是廣東的李鐵夫,他于1887年到英國和美國去學油畫。學成之后,在歐美舉行的藝術大賽之中,屢獲大獎。廣東是富有革命精神和創新激情的一片熱土,自近現代以來,廣東一直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上,在全國享有“領風氣之先”的美譽。近現代的廣東本土上,有諸如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和黃少強為代表的有影響的嶺南畫派,有以李鐵夫為杰出代表的名揚海內外的著名革命家兼油畫家,還有從廣東走出去,活躍在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和海外,被譽為中國近現代美術奠基人、開創者和建設者,為中國近現代美術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林風眠、李金發、何香凝、司徒喬、潘思同、董希文、方璧君、丁衍庸、趙少昂、楊善琛、陳大羽、李樺、羅工柳、古元、鄭可、關良、羅銘、張望和方成等一大批美術家。
新中國美術中的廣東現象
新中國成立以后,廣東美術沒有停止探索,創造了多個藝術高峰,其中一個是20世紀50年代"全盤蘇化"時期,以"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為標準,大搞民族虛無主義,批判"中國畫不科學",要求國畫家必須補畫素描石膏像的課。當時廣東美術界沒有強迫國畫家們去補畫素描石膏像的課,這說明了廣東美術家不喜歡在政治上跟風和趕時髦。另一個高峰就是十年文革中的“廣東現象”。
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鳳蓮在著作《新時期廣州文藝批評之路》中專章介紹說,文革時期,全國藝術創作普遍受政治枷鎖的禁錮,而廣東美術界仍然一片繁榮:國油版雕以及其他畫種均衡發展,畫家群星璀璨,而且打破了畫種的局限;廣東美術的創作在新中國美術的整體上處于第一陣營,廣東美術家們的個體創作也持續發展,從無間斷。廣東美術家在二十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際遇和獨樹一幟的風格,折射出全能政治年代中的中國藝術的發展邏輯,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孕育自南方文化的蓬勃生機和巨大的創造才華。這一時期可能是1949年以后廣東現代美術以整體形象出現在全國美術界的最輝煌時期,潘鶴、楊之光、湯小銘、唐大禧、陳衍寧、潘嘉俊、伍啟中、林墉、鷗洋、陳永鏘、尹國良、邵增虎、林豐俗、梁照堂等廣東藝術家在當時的全國美術界都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們的作品從總體上在新中國的美術史上占據了非常醒目的位置。
對此,廣州美術學院副教授、策展人胡斌舉例告訴我:“邵增虎的《農機專家之死》、廖冰兄的《自嘲》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作品,但是我們現在說到傷痕美術的時候就很自然地想到四川的一些畫家,其實在廣州也有很重要的表現,它們應該進入到這樣一種歷史敘述當中。”
當代美術的廣東現場
近年來關注廣東當代美術現狀的胡斌為信息時報記者做了梳理:一般我們認為當代美術在全國范圍內是從星星美展開始的,在廣東,大概80年代初李正天等畫家的團體“105畫室”和稍后的“南方藝術家沙龍”開始有對現代美術的一些探索,與85新潮等全國范圍內的美術探索是一致的。此時,廣州是改革開放的前沿,藝術與商業的結合、尤其是設計走得比較前,因此對現當代藝術的探索表現稍弱,但也不代表就沒有一些現當代藝術家在進行藝術的探索。胡斌舉了鄧箭今在表達主題上與北方“新生代”的合拍為例:“他也是消解宏大敘事,講述身邊的生活,他在對應北方,但是有南方的特點,也就是黃專老師所說的"超越新生代"。對應北方的消極、無聊,他顯得更加積極、健康、陽光一些。”
胡斌認為,90年代以來廣東美術有兩個重要的傾向,一個是“大尾象”他們對于城市空間的富有觀念性的、智趣的介入,這在全國來說是有標新立異的感覺,持續的時間也很長;另一個是在水墨的“后嶺南”之后不久,黃一瀚等人提出的“卡通一代”,也是對城市新潮現象的表達,但是與北方城市現象的表達相比采用了更積極的一種態度。胡斌說:“前者代表一種觀念性的、富有智趣的研究和討論,像學院里面也有這樣一些人,比如陳侗,他們和原大尾象成員、維他命藝術空間、陽江組、以及國際策展人侯瀚如等,體現出某種精神意涵上的相似性。后者傾向于偏符號化一點的、偏圖像的表達,在年輕畫家中體現的比較充分,這基本是廣州當代藝術的一種格局。當然,在這兩種大的傾向中間還有許多個體性的,很難歸納的探索。”
“卡通一代”在廣東提出之后,類似的傾向卻反而在四川得到了迅猛發展,以至于全國美術界通常認為這種符號化的、圖示的研究的傾向四川是一個代表性的表達。胡斌說:“廣州這里很容易誕生一些新的潮流、激發出一個新的現象,但是缺乏一個足夠的持續力量把它保存下來,也沒有那種集結成群的力量,各自為政,各做各的。我覺得這更多的是一個優點,藝術探索更多的還是應該是個體的。但肯定會影響到它作為一個整體力量在全國的呈現。個體性是一方面,但藝術發展還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生態,這個生態是從藝術家創作到各類空間的支持,包括院校、民間、公立的空間的支持,包括批評的理論的介入,包括藝術市場、博覽會、畫廊等各種機構的完善,從藝術到機構,從展覽到批評,要有完整的鏈條,這個區域才能活躍起來,不管是學術還是商業。廣州雖然已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整體上收藏的培植、市場的發展、支持當代藝術的機構……還是比較弱。從批評力量來說,廣東的藝術理論在全國絕對是走在前列的,但是沒有形成一個整體的力量,很多都沒有跟廣東的當代藝術的生產現場緊密聯系起來,對本土的藝術生態沒有足夠的呈現。”來源信息時報)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