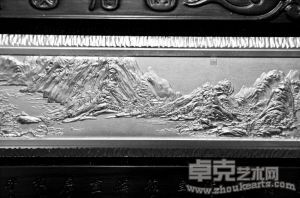
純金版浮雕富春山居圖合屏近日在深首次發布。(資料圖片)

《富春山居圖》600年的收藏歷史上,曾經有四五十年,一直保存在宜興吳氏家中。(資料圖片)

分居兩岸60年的《富春山居圖》在臺北故宮合璧展出,也引出了一段《富春山居圖》與吳氏家族的傳奇故事。(資料圖片)
分居兩岸60年的《富春山居圖》在臺北故宮合璧展出,成為2011年中國文化界的盛事,《富春山居圖》這幅傳世名畫也再次聲名鵲起,進入公眾視野。9月中旬,深圳百泰打造的純金版浮雕富春山居圖合屏在深圳首次發布,同時,這次發布會請來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先生之子吳歡作為嘉賓,引出了一段《富春山居圖》與吳氏家族的傳奇故事。面對本報記者,吳歡先生首次披露這段鮮為人知的名畫奇緣。
后人回鄉辦展
獲知名畫奇緣
吳歡生在曾被外刊評論為中國最大文化家族的吳氏家族,他的祖父是故宮博物院創始人之一、書畫大師吳瀛,父親是當代著名劇作家吳祖光,母親是著名評劇表演藝術家新鳳霞。再往上數,從明朝追溯下來的二十幾代中,吳家出了17個進士探花,隔幾代就會出知名人物。而吳家與《富春山居圖》的淵源,吳歡自己也是在今年6月回鄉辦展時得知的。
“我祖籍常州,也知道我們家祖上是從宜興遷過來的,不過,從來沒有到宜興去過。”2011年六月,吳歡應邀到常州舉辦回鄉展覽,在展覽開幕式上,他結識了江蘇宜興美術館館長劉明和副館長邢娟。“你知道常州吳氏是從宜興遷過去的嗎?”“你知道你們家和《富春山居圖》有很深的淵源嗎?”面對兩位學者的前一個問題,吳歡的回答是肯定的,面對后一個問題,吳歡還真有點迷茫。在宜興美術館的盛情邀請下,吳歡第一次回到了宜興,并在宜興文昌閣里,找到了祖先的名字。
此次在常州辦展,主辦方贈送給吳歡的禮物正是一本吳氏家譜。其中第一個名字是明代進士吳性,最后一個名字正是吳歡的祖父吳瀛。而在宜興的文昌閣明朝進士名錄排序中,緊隨正德九年(1514年)進士吳仕之后的正是嘉靖14年(1535年)進士吳性。“兩人可能是兄弟或者堂房兄弟。”
在尋根問祖的同時,吳歡也第一次聽到了吳氏家族與《富春山居圖》的深厚淵源。原來在《富春山居圖》600年的收藏歷史上,曾經有四五十年,一直保存在宜興吳氏家中。而在此前此后,又有多位吳氏家族成員與這幅名畫發生關系,在這幅傳世名作的收藏、毀壞、修復甚至南遷中,都能看到宜興吳氏子弟的影子。以至于宜興美術館副館長邢娟特別撰寫“《富春山居圖》與宜興吳氏解密”一文記敘其事,并感嘆這是一段“讓人拍案稱奇的奇緣”。
幾代吳氏后人
結緣“富春山居”
《富春山居圖》的第一位收藏者是黃公望的道友無用師。至明代畫家沈周收藏前的一百多年中,收藏情況不明。因此,沈周成為《富春山居圖》有史料記載的第二個重要收藏人。而沈周與一生偏嗜茗茶的宜興吳綸吳仕父子過從甚密。沈周之后,《富春山居圖》輾轉多人之手,最終畫落吳綸吳仕后人吳洪裕之手,這可說是一大奇緣。
吳家第一個拿到《富春山居圖》的人是吳仕的兒子吳達可,其子吳正志,與明代大畫家董其昌同為萬歷17年同科進士。明萬歷24年董其昌購得此卷。董其昌晚年遭難,迫不得已以重價把《富春山居圖》典押給好友吳家,以期過后境遇好轉贖回,但最終未能如愿。拿到畫后,吳達可的兒子吳正志就在畫上六張紙的騎縫處都蓋了自己的“吳正志”和“吳之矩”的收藏印。300多年后,吳之矩騎縫印作為最有力憑證,幫助著名鑒定家徐邦達先生最終確定《無用師卷》為真跡。
《富春山居圖》在明代萬歷年間至清代康熙初年四五十年間,一直保管在宜興吳氏家中。吳正志在萬歷末年逝世,這張畫就傳到他的幼子吳洪裕手中。在富春山居圖的收藏史上,吳洪裕是最不可跳過的名字,可以說他既是這幅名畫的知己,也是這幅名畫的劫難。
據說吳洪裕極為喜愛此畫,每天不思茶飯地觀賞臨摹,到了朝夕不離的地步。惲南田在《甌香館畫跋》中曾經記載:吳洪裕于“國變時”置其家藏于不顧,惟獨隨身帶了《富春山居圖》和《智永法師千字文真跡》逃難。可見對這幅畫的癡迷程度。而正是這種癡迷,給這幅傳世名畫帶來了它在人世的第一場大劫難。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富春山居圖》
最癡迷的收藏者
清順治七年,臥病在床的吳洪裕到了彌留之際,氣如游絲的他念念不忘《富春山居圖》,竟然要以此畫“火殉”,萬幸的是,就在畫即將付之一炬的危急時刻,從人群里猛地竄出一個人,“疾趨焚所”,抓住火中的畫用力一甩,“起紅爐而出之”,愣是把畫搶救了出來,他就是吳洪裕的侄子,名字叫吳靜庵。為了掩人耳目,他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畫,用偷梁換柱的辦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圖》。
畫雖然被救下來了,卻在中間燒出幾個連珠洞,斷為一大一小兩段,此畫起首一段已燒去,所幸存者,也是火痕斑斑了。
1652年,吳家子弟吳寄谷得到畫后,將此損卷燒焦部分細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幾乎看不出是經剪裁后拼接而成的。于是,人們就把這一部分稱作《剩山圖》。而保留了原畫主體內容的另外一段,在裝裱時為掩蓋火燒痕跡,特意將原本位于畫尾的董其昌題跋切割下來放在畫首,這便是后來乾隆得到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至此,原《富春山居圖》被分割成《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和《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長短兩部分,身首各異。從此各有際遇。
首次披露
收藏故事
《富春山居圖》的前后兩段后來分別流入不同的收藏家手中,其中《無用師卷》乾隆年間進入皇宮,卻被當作贗品收藏了200年,直到故宮文物南遷才沉冤得雪。而《剩山圖》則在抗戰期間,為大畫家吳湖帆所得。誰能想到,這兩幅畫都再一次與吳氏后人結緣。這位有緣人就是吳歡的祖父、收藏家吳瀛。
吳瀛是著名劇作家吳祖光之父,故宮博物院創辦人之一。他于1913年來到北京,任民國北京市政府坐辦(秘書長),接管清宮。1924年參與創辦故宮,被民國政府委任紫禁城“接受代表”,首任“故宮博物院常委”、“古物審定專門委員”、《故宮書畫集》首任主編,在當時的文化界舉足輕重。同時,他也是故宮文物南遷的監運員。在抗戰烽火燃遍全國的時候,《無用師卷》與600多萬件故宮文物一起,10余年中歷盡艱辛坎坷,行程數萬公里,輾轉運抵南京、四川、貴州……至抗戰結束后,陸續運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運至臺灣。從此,《無用師卷》與《剩山圖》兩岸分離60多年。而經過考證,學者發現《剩山圖》的最后一位私人收藏者吳湖帆,出身浙江吳氏,也與宜興吳氏有著姻親關系。
一幅傳世名畫,與一個文化家族,輾轉數百年,結下不解情緣。2010年,《富春山居圖》因溫家寶總理的一句“畫是如此,人何以堪”而名聲大噪,也使得一段沉埋的收藏故事大白于天下。
吳歡指點大眾收藏
玩假文物,悟真文化
出生于書香世家的吳歡,有一位大收藏家祖父,但對收藏,他卻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他曾經放言,“要玩就玩假的”“玩真的是玩命”,這句話應該怎么理解?作為收藏家族的后代,吳歡是怎么看待今天的收藏熱?本報記者就此問題專訪了吳歡。
吳歡的祖父吳瀛先生不僅是故宮博物院的創始人之一,而且是一位知名的收藏家、文物鑒定專家,他一生癡迷收藏,后來把自己珍藏的文物字畫,捐獻給故宮博物院。其中古代一些金、銀、玉、瓷及呂紀、石濤、鄭板橋、八大山人、文徵明、唐伯虎等人的書畫均為國寶,有連城之價。其中絕大部分為國家一級文物,共計241件。1985年,《人民政協報》曾發表了一篇文章,故宮博物院列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給國家捐贈文物貢獻最大的300位大家,赫然頭一名便是吳瀛先生。
吳歡的父親吳祖光和母親新鳳霞都是文化名人。作為著名演員,新鳳霞那時候收入很高,“別人掙18元工資的時候,我媽就掙1200元了,我爸爸從香港回來,稿酬也很高,所以在那時的文化人家庭里,我們家算很有錢的。”據吳歡介紹,那時候,父親經常買了齊白石先生的畫作贈送給友人。“我們家是很早就推崇齊白石的,齊白石的畫才10元一張的時候就買了很多,經我們家手送出去的齊白石畫至少有四五百張。”
出生在這樣一個文化世家,吳歡從小耳濡目染,天然地對文化藝術有了非凡的感悟力,他三歲開始隨祖父習字,后來由字入畫,成為著名的書畫家。對于家庭的文化氛圍對自己的影響,吳歡并不諱言。但對于祖父癡迷收藏不惜傾家蕩產卻不以為然,這也是他的名言“要玩就玩假的”“玩真的是玩命”這句話的由來。吳歡說,動輒幾百上千萬的真文物沒多少人能玩得起。祖父一生致力于中國古代文物的收藏,為此不惜負債累累,以致妻子兒女皆受累于此,嚴重的時候,甚至連孩子的學費都交不起,為此常常和妻子吵架,弄得家里雞飛狗跳。“我從小跟著奶奶長大,直到祖父去世后多年,奶奶還常常為此埋怨祖父。”所以,吳歡認為,收藏熱是件好事。收藏是人類對文化的崇拜,今天這種崇拜成了流行時尚,對文化的傳承非常重要,對每個人來說,收藏都可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但同時,收藏也不能走火入魔。“有能力盡可以玩真的,但對于普通大眾,我提倡玩假的。一般家庭完全可以玩假文物,真文化。收藏更重要的是收藏文化。”吳歡希望,今天的收藏者們別進入誤區。
此次深圳之行,吳歡是專程前來參加百泰純金版浮雕富春山居圖合屏的首發式,對于用純金浮雕的方式重現富春山居圖,吳歡表示非常支持。這不僅出于吳氏家族與《富春山居圖》的奇緣和吳歡本人對這幅名作的喜愛,更是源于他對用商業推廣文化的提倡。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老一代文化人還在反對藝術商品化的時候,吳歡就提出“我反對藝術商品化,但我提倡商品藝術化”。吳歡認為,在今天的社會,商業行為代表著文明與進步,通過商業手段推動藝術傳播,可以讓藝術走得更遠,中國的歷史文化成就可以通過商業行為在現代延續生命,使它們的文化含義得到推廣。“百泰用黃金打造《富春山居圖》總比純粹地收藏金磚更有文化含量,這不失為一種科學的行為,這種設計和創意,我支持。”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